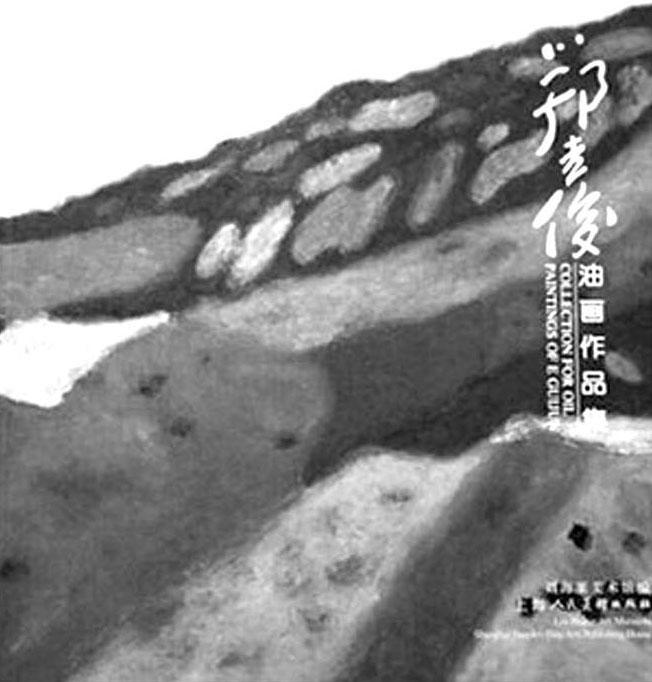目录
鄂圭俊
一、从影院美术杂工走向专业画家
鄂圭俊
1942年3月,鄂圭俊出生在青海西宁一个土族家庭。
土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东南麓及黄河、湟水、大通河和洮河流域,与那里的汉、藏、回、蒙古等民族人民生活在一起。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纯朴的土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这片肥沃、神奇的土地,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尽管有关少年时代的生平资料极为稀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民族长期生存的这块土地以及自己民族的文化,对鄂圭俊的艺术创作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精神气韵,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无不体现着他对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和人民的魂牵梦绕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末,鄂圭俊就读于青海省文化艺术学校。1960年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红旗电影院、西宁文化馆工作。在电影院,他做过美术杂工,大致是写招贴、画海报一类的事情;在文化馆,工作也相差无几。业余时间,他自学绘画。起初学国画和版画,后来因为色彩感觉特别好,又改学油画,并不断进行艺术创作。就这样,经过了整整20年。
美术评论家范迪安对鄂圭俊的成长道路有过中肯的评价:“鄂圭俊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少数民族画家,他从少年学画到青年时代以美术工作谋生,经历了许多生活的磨难,甚至形成了他不善言辞、朴素沉稳的性格,但是他的艺术禀赋和才能却是充分的,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期,他也能沉浸在专注的艺术感受和表达中,画出有灵气和内涵充实的作品。他从一个电影院的美术杂工走向专业画家的道路,很能证明他对艺术执着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
正是经过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鄂圭俊的艺术才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调入青海省文联,担任文联杂志《青海潮》的美术编辑,同时在美协青海分会工作。在这段时间,他还担任过青海省青联委员、青海省对外友协理事等职。
1979年,鄂圭俊的油画作品第一次被选中参加全国性的美展,到1984年,在5年之中,他就有9幅作品获选参加全国性美展。他的作品在全国性展览中屡获荣誉,1982年,油画《迎新娘》获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版画《农家》获全国第八届版画展览优秀奖,油画《春的脚步》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铜牌奖。此外,《高原情》《套牛》《远客》等先后获青海省级文化创作奖8次。他还有许多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协对外版画展览,日本的“现代中国优秀作品展览”,东德柏林举行的国际版画展览等。
作品《春的脚步》
二、大写的西部风情
1987年,鄂圭俊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任专职油画家。
尽管从边远的青海高原来到了繁华都市,但鄂圭俊仍旧是乡音无改,而且一段时间里,绘画作品题材和风格,也都延续了在青海时的面貌;即便是后来艺术创作的突破,也没有离开西部原野的风貌和精神。
有评论家说:“鄂圭俊先生出生并成长于中国西部的青海省,这很直接地为他的油画艺术尤其是早期油画艺术提供了天然的绘画素材和个人观照。青海湖畔的神秘与灵动,青藏高原的浑厚与崇高,乃至庄严的宗教寺庙、古代遗址和纷繁多样的少数民族风俗民情,都成为鄂先生作品的灵感来源;加之其土族的文化身份,更容易认同并接纳这些自然灵魂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仅如此,淳朴、淡泊而悠远的中国西部风土特征也孕育了他的豁达、纯粹的个人气质,这从他的作品中亦能感受得到。”
评论界一般把鄂圭俊的创作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创作起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是90年代末期至今。这两个时期的作品,虽然都没有离开青海高原的西部原野,但无论艺术技巧、审美取向还是精神意涵,都体现出既有联系又显著不同的特点。
鄂圭俊前期的作品,人们一般会用“风情”来概括,即主题是西部民族风情,包括生产、生活活动等。早期的获奖作品,如油画《迎新娘》《高原情》《套牛》《远客》,版画《农家》等,都是如此;但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纯然写实,构图、造型上都有大胆的开拓。比如获第六届全展铜牌奖的油画《春的脚步》,它以青海土族“六月六”的花儿会为题材,表现了土族青年在春的原野上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画面充满了欢快的视觉节奏,弥漫通幅的绿色尤其洋溢出活跃的生机,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在改革初期涌动的蓬勃气象,而在造型上则大胆吸收融汇了西方立体主义的造型手法。这幅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在当时的画坛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入藏于中国美术馆之后,每逢组织反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的展览,总会再一次特别展示。
到上海以后,尽管主题还是“风情”,但审美取向和表现手法逐渐有了一定的改变。时空的转换,使他得以远距离地观照、体会以至思考,从而抓住民族风情更为本质的东西,从再现过渡到表现。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唐蕃古道》(1988)创造了一个神奇、璀璨的梦幻世界,充溢着肃穆庄重的历史感;《少女与牛》(1988),在整体浑廓中造成空灵、游动和对比之趣,弥漫着真情与活力;《赛牦牛》(1990)将生命激情化作运行于天地间的一团火焰,迸发着生命的闪光。
诚如一篇评论所言,“鄂圭俊全身心地体验青海高原自然人情,把对乡土民族文化的热爱转化为主体内在精神的映象,引发出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和激情”。不过,“风情”之于鄂圭俊的创作,已非仅题材的获取,也非形式的偏好,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符号——主观地成为画家精神的外化显现,客观地形成图式结构的文化显现,从而构成“风情”的超越。这种风情是物与我、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古代和现代的统一,是一种大写的“风情”。
三、“大自然”系列的自我超越
对于鄂圭俊的个性,有人有过精到的概括:与世俗离得较远,离艺术很近(张培成语)。他不善言谈,与人交往无多,只是踏踏实实地画自己的画。在当今这个艺术家纷纷陷入世俗物欲的时代,鄂圭俊仍旧沉静着,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艺术园地。也因此,他与画坛似乎若即若离。其形象亦时隐时现。就是在这种沉静与坚守中,他获得了自己艺术的突破与升华,并又一次令画坛震撼。
20世纪90年代末期,鄂圭俊推出了自己的“大自然”系列。这一系列作品通称“大自然”,每幅作品并没有具体的标题,仅此就体现了作者对题材的概括把握和作品所显示的宏阔气象。而实际上正是这样的,诚如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张培成指出的,“鄂圭俊的大自然中几乎看不到清泉小溪或是庭院深深的人间佳境,也不见茂林修竹、春花秋月,我们能看到的往往是那些个沧溟的大漠、奔腾的长河、无云的苍穹、残雪泛银、黑沉沉的山谷……那些画面让你无法与精巧、玲珑相关联。在他的许多风景油画中几乎无甚细部让你去揣摩,画面上往往就是那么沉静的几根水平线或是大小组合的几个团块。那种简约与精练却化成了雄强、浑厚的力量,直击你的心灵深处。犹如拨动大提琴的琴弦而发出沉闷的回响。面对他的作品你绝不会陷入对于一些细节的咀嚼之中,因为扑面而来的就是那苍凉的大漠、群峰、江河,这是一种气魄更是一种格调”。
关于鄂圭俊这一时期作品的特点,评论家们用“简约”“单纯”“宁静”等词语来概括,也有评论家将其概括为与前期“建构自己”不同的“超越自己”,这些从绘画技法或者艺术精神方面的把握,都道出了“大自然”系列的特色。
“简约”“单纯”是“大自然”系列构图、色彩等的突出特点。画面作平面化的处理,有时又有焦点式透视的假象,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空间,正是这种远离于真实的空间使画作有着直指精神的力量。自然界中丰富繁杂的树、石、山谷,都被画家浓缩成浑圆大气的团块,纷繁琐细的自然外形全被舍弃,主观理性的安排布置直击主题。色彩有时近于浓丽,纯净的黄、火焰样的红并置,热烈而又谐和;青翠的草绿间划过几痕玫瑰红的色块,艳丽而又不喧闹;其间以一些乌黑的线条叠缀色块之间,面积极小,似乎匆匆而过,却又必不可少。简约明快的图式,浓烈的装饰意趣,艳而不俗的色彩,使这些画作特立独出。
鄂圭俊在自己的作品展上讲话
鄂圭俊自学成才,并非油画科班出身,因此油画的条条框框于他不太相干,而他超强的色彩感觉又为油画所必须;他能书能画,油画、版画兼擅,绘画技法能够在跨领域间灵活借鉴和转换;他早年学过国画,古人山水画的写意精神,又给了他巨大的启迪。正是这些,成就了他独特的油画艺术。他说:“我所呈现的‘大自然’系列正是我近年来以适合自己个性的现代形式,试图表达出宋元时期山水画那样,是生命与宇宙的圆融,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使观赏者除视觉上的和谐外,产生宁静致远的精神反射。”
鄂圭俊后期的作品有了一定的宗教因素,这似乎是精神追求与超越的必然。这种因素,不只是表现在他创作了一些宗教题材的作品,比如《菩萨》等;更在于作品中体现出的宗教精神。鄂圭俊并不是佛教徒,但后来这些年,他每天早晨会默诵几遍《心经》《大悲咒》或者其他的佛教偈语,以此求得心灵的宁静和升华。
《鄂圭俊油画作品集》书影
鄂圭俊的画作参加了十多次国内外的美术作品大展,画种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有版画、油画,后来则均为油画;在国外的展览,主要是日本和德国。个展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1998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了“鄂圭俊油画作品学术展”;2006年,上海富大画廊举办了“曾经与现在——鄂圭俊油画作品展”;2008年,由刘海粟美术馆和上海油画雕塑院共同主办“大自然系列——鄂圭俊油画作品展”;2011年,青海师范大学举办了“鄂圭俊作品观摩展”。
鄂圭俊的一些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收藏,并入选《中国美术馆藏画选》《中国当代油画集》等大型画集。他还出版有《鄂圭俊油画作品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