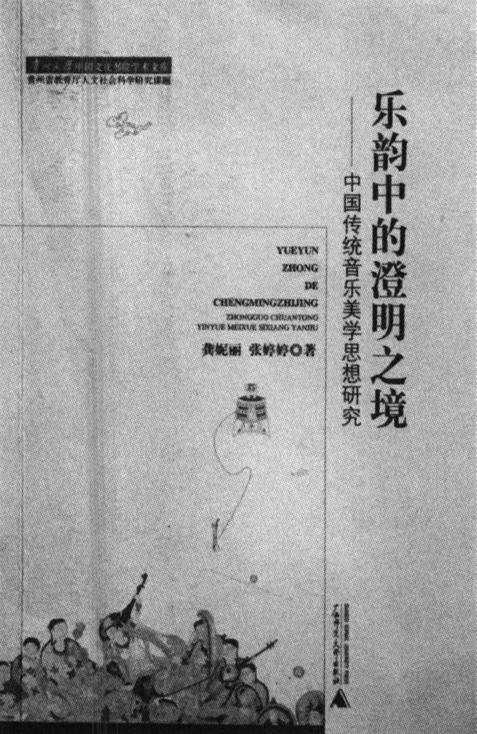9 张新民
张新民
采访前言
我对专注于学术的人一向心存敬意。尊敬的方式,一是充满好奇,哪怕自己不学无术,也还是很关心这些有学问的人的人生路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悟,以便知道我的人生距离“偶像模式”,到底是“想都别想”还是“有点盼头”;二是一旦产生交集,尽量多听少说,绝不虚张声势,避免言多必失——“藏拙”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给从未谋面的张新民老师发去采访提纲,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尽管开头的称呼不怎么严肃,很有挤兑我的嫌疑,但信的内容一如他的历史专业,“古色古香”,充满“时光感”。见到采访被接受,我一边欣喜,一边却不动声色——没有回信,因为作为一个修为不够的“江湖混混”,我的功力实在不够我自如地把话说得“古色古香”。
倒是被我拉来当“中介”,帮我转交采访提纲的王尧礼,省文史馆年轻的学者,在把张老师的信转发给我之后,又顺手帮我做了回复,以免无礼:“张师慨允,尧礼及愚友舒畅女士已欢喜过望。尧礼谨候”——“愚友”不是谦词,在这里就是实事求是。
半个月后,张老师按时“交作业”来了。答卷仍然通过王尧礼转交,也仍然附了短信:
我还是没回信——用贵阳话说就是“雀起”(“鸦雀无声”,默默躲起)。这种古色古香的“高冷范儿”,我真心hold不住。
这两封信,还有张老师的学术成就,让我在打开张老师的答卷之前,做足了陷入一堆拗口文字和艰深理论的思想准备。但事实证明,我在和学者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过招中都稳占下风。张老师的答案如此平易活泼、自然清通,而我原本蓄足的力气、攥紧的拳头,活生生打在了棉花上。读着那些面目可亲又饶有趣味的文字时,我几乎有些喜出望外——原来学问高深的人也很会聊天的啊,哪会故弄玄虚。知道在什么地方不厌其烦地“精益求精”,又在什么时候善解人意地“化繁为简”,这是智商太高,还是人品太好?
就在收到这份答卷之后没几天,在安顺普定,我和张老师第一次“接头”。我们一起参加省文史馆《民国贵州文献大系·匏斋集》首发式,并前往参观任可澄先生的村中故居。张老师在首发式上发言,谈任可澄对贵州文献的意义。他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如烟往事在他那里都成了可以随意拨拉的算盘珠。发言完毕,会议主持人顾久先生说,张老师身上有着很多和任老先生相通的气质,比如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修史传世的使命感,等等,“如果任老先生见到张老师,一定会引为知己!”
回贵阳后的一天,我去张老师家翻拍老照片,只有他的夫人龚妮丽在家。龚老师虽然自己也是贵州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美学研究专家,但退休以后更多的精力却都用来当张老师的专职秘书和生活陪护了。她领着我一间一间参观张老师那些顶天立地、塞得满当当的书架,还有溢出书架、“堆山摞山”的书。每个书呆子的书房外,都有一个想收拾却被禁止收拾的主妇;每个潜心学问的学者背后,也都有一个甘心“打下手”的妻子。这几乎是一系列“小舒请教”下来,我接触到的普遍规律。
张老师原本要做的唯一的家务是洗碗,最近也被龚老师“炒鱿鱼”了,原因是:“他洗个碗下来,自己倒被洗脏了,还把厨房洗得更脏。”说到张老师的口才,龚老师说他是从来没发言稿的,关键的字句就顺手写在牛皮纸信封上,揣在兜里,需要时拿出来看看。据说有他的“粉丝”学生,为了模仿偶像,也把东西记在牛皮纸信封上,龚老师跟我笑说:“学生不知道,他之所以用信封,其实是因为喜欢胡乱揣着,牛皮纸的更耐磨……”
那个下午,喝着龚老师泡的咖啡(泡咖啡的时候,听她在厨房里说:唉,杯子也是缺了口的,真是不好意思……),翻看她和张老师从学生时代开始的照片(最早的竟然是两人在花溪中学就读时的学生证照片),时间飞快。临走时龚老师送我一本书,《乐韵中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是她和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的女儿张婷婷合写的,而作序的正是张新民老师。用一本学术书装进一家三口的合奏,有情有理,琴瑟和鸣,这是多独特又会心的方式。
(注: 张新民夫妇也是花溪中学(现清华中学)校友。)
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
小舒请教之提问张新民
1
“特别特别学术”岂敢,“特别特别近视”倒是真的。其实不仅是“近视”,根本就是“半瞎”,只能说比“盲人”稍好一点。1984年到上海做视网膜剥离愈合手术,出院时医生就郑重劝告:“必须立即改行,不能做任何文字工作。”但是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好像是跟医生“对着干”,每天看书写作的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眼睛倒是越来越坏,文字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所以我常开玩笑说;“除了天命,什么都不要相信——尤其是医生。”“知天命”是孔子五十岁才有的境界,不想眼睛“瞎”也让我很早就获得了一个补偿性的礼物——“知天命”。
其实父母给我的本来是双好眼睛,年轻时还有人劝我去考飞行员呢!是我自己胡乱读书给弄坏了,主要是下乡时在煤油灯下拼命看书,总想把白天干活的时间补回来,结果一直到今天,学问没有做出来,样子却让人以为读书多。这是“半盲半视”给人造成的错觉,好像读书多就一定戴眼镜似的。视力的好坏根本就不是学问大小的先决条件,否则一看见戴眼镜的人就跑去请教学问,往往不是碰钉子就是闹笑话,较诸“以貌取人”又凭空多了一个“以镜取人”的笑料。
不过,经常闹笑话的倒是我自己,走在街上与人打招呼,往往错认“张三”为“李四”;一人去挤公交车,经常把10元当成1元钱扔到收费箱去;最近家中干了30年的洗碗“职业”也给开除了,因为“从来”就洗不干净。但了解我视力不好的人,大多能善解人意,“宽大”我所犯的错误;我也以视力不好为托词,尽量少做应酬周旋的事。视力不好已成了我的挡箭牌,让我更好地躲进自己的书籍世界,自由自在读我想读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
真正的读书人都会“痴书”,从年轻时见书就买,现在将近200平方米的住房,几乎全用来做堆书之用了。老伴时常会半生气地教训说:“除了厨房和厕所,你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堆书。”“痴书”久了人也会变成“痴人”,一次拿着伞去还给我所供职的书院,半路下雨了却不知道撑开遮雨,熟人看见了很惊讶,问为什么不打伞,我才突然明白原来还公家的伞也可以临时用来为私人遮雨,这样就不会弄得自己满身雨水。回到家还说童书业在校园散步却找不到自己就在校园附近的家,想为自己解嘲,不想事情早已变成掌故,风传校园,大家都以为比童书业更搞笑。“痴”是不是学者的“职业病”我不知道,但从《史记》到《世说新语》到《红楼梦》一路读下来,你就会发现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他们“痴书”“痴情”“痴义”“痴价值”“痴理想”,即使别人认为他们是“痴人说梦”,他们也心甘情愿地一“痴”到底。
谈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说不辛苦,但也其乐无穷,令人万分痴迷。鲁迅说嗜好读书就像天天打牌一样,真正的目的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读书是这样,学术研究更是这样,只有完全脱去功利的羁绊,真正浸入认知的妙境中,苦就统统转化为乐,乐也成为苦乐一体的“大乐”了。这就好像孤身一人,层层拾级登上凌云绝顶,凭空俯瞰天下美景,胸内尘埃一概洗尽,人便步入了忘人忘己的妙乐至境。法国学者梅里特认为即使“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每一个在学术的精神天地遨游的人,都会知道他说的话决非一时偶然的虚语。
当然,学术研究的乐趣主要在于认知和发现,但认知和发现依然离不开读书,“痴迷”书籍的世界其实就是“痴迷”学术的世界。陆游曾有诗说:“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需书卷作良医。”借用他的说法,我想我和大多数学人一样,不仅不想治好自己“痴迷”已久的“职业病”,反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忘老”“防病”。防什么病?当然是俗气之病,浅薄之病,人云亦云之病,否则便谈不上自己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至于你所说的“神秘”,那倒大可不必,因为知识的大门为人人敞开,人人均可以进去。但却应该“敬畏”,因为能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并不多,我们当然应该佩服那些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敬畏就是佩服感的升华,我们没有理由不敬畏那些为学术献身的人。
2
学者观察世界的方式,当然有别于记者和艺术家,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之处也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是学者必须谨慎地守着他的学术纪律,严格地按照论证的逻辑程序一层一层地阐述或宣讲,即使中间可以容许必要的推测或想象力,但也必须满足事实结果的真与学理的自我圆足两个条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任何学者都必须从事大量材料取证的工作,材料取证到手后,又有一系列的分析归纳方法要做,最后则按照逻辑程序一步一步地整理成文,中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可省。这当然也可看成是一种“表幽阐微”的工作,它要抗拒的正是人类社会经常出现的记忆遗忘——譬如我们今天就遗忘了不少抗战史实,“文革”长期不研究也难免同样的命运,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有责任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就是还原真理本来应该有的“真”。因此,学者与记者一样,也需要对世界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能力,只是他们还要将眼光延伸至遥远的古代,在现实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便对他们研究的对象做出合理正确的解释。任何严谨的学者都必须具备求真的精神,但未必就不可以像艺术家那样发挥想象,合理的想象力的发挥乃是创造性工作的灵思源泉,真理的诗意化表达,价值的艺术化传递,都在一定程度为有生命的学术所允许。只是最后仍必须经过小心谨慎的求证,证伪作为可能永远都必须无限开放。
真正拥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一方面应该遨游在思想的天地中,好似乘风御云的仙人,一方面又必须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犹如田间地头耕耘劳作的农夫。他既要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永远不丧失自己的批判精神,又要积极勇敢地投入现实世界,了解一个时代气运升降转移的节律。这是与现实世界不即不离的一种关系,太近太远都不利于观察,观察永远都为睿智的学者所必须。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说要锻炼“隔离”的智慧,显得太消极;我近年主张“旁观”的智慧,稍有一点积极。“旁观”主要取意《周易》的“观卦”,老子也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观复”也是培养“旁观”智慧的一种方法。“旁观者清”才能更好地锻炼我们的观察睿智,培养我们的学术批判精神。
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当然就会对某些世俗现象“视而不见”,也就是你所说的“呆萌”或“低能”。譬如我就从不喜欢去超市,经常是站在门外等老伴。别人津津乐道的市场物价,我真可说是一无所知。80年代末物价疯涨,几位武汉大学的朋友闲聊时,问我贵阳鸡蛋的价格,我随口报了个价,回到家却被“臭骂”了一顿,原来是错将70年代的价搬到了80年代,让别人误认为贵阳生活最“小康”了。2002年离开师大到贵大,校内有老师叹息说:“可惜学校最后一个书呆子走了。”“书呆子”换个说法就是“迂阔”,在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只能是“另类”。
(注: 1969年,瓮安,张新民(右二)和生产队队长、农民和同学在一起。图中的狗狗和张新民感情最好,因此得名“张赛虎”。)
3
我其实应该是1984年毕业,眼睛手术又多拖了一年。那时候贵阳人口少,考上研究生好像全城都知道似的。读研究生时并没有上什么课,完全靠自修阅读,整天在图书馆泡,除了睡觉几乎全部时间都在读书。撰写毕业论文时问应达到什么水平,回答是至少副教授水平。80年代初期你知道大学有多少副教授吗?恐怕整个学校屈指也不能满数。不上课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自由地阅读真是人生最惬意的事。这种不严格考试的做法还可追溯到“文革”前,因为那时“政治挂帅”主宰了一切,成绩好不好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考试——包括为数不少的开卷考试——之简单总是令人出乎意料,偷看“闲书”反而让人更感到乐趣。因而我一生没有太多的考试记忆,反而是到处找书看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从事学术研究当然有“天性”的原因,因为除了读书之外我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长处。然而命运的“安排”也很重要,因为它总是以“召唤”的方式引领我向前。短期看好像总是自己在选择人生,终极地看则一切都归于宿命。历史的可能性只在事件刚发生时如潮水般涌来,事件结束潮水退去则一切都归于宿命。这样说并非要否定人的主体积极性,而是说人在积极努力的同时,也要知道生命的局限和世事的无常,只问自己是不是真正耕耘劳作了,是否有收获则大可不必计较。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强调“为己之学”的重要,一切都以生命价值的充分展开和实现为转移,满脑子功利的学生总是会受到我的呵斥,或者干脆就拒之于门外。
4
1980年代初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人心民意都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上升期。政治的冰川期解冻了,春天的气息到处都可以触摸到。大学完全没有功利意识,学术的氛围四处弥漫。我读的专业就招了我一个人,简直就是独生子女,全校文科研究生寥寥数人,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前辈学者的告诫是五十岁以前尽量少发表文章,否则即使顾颉刚(我的老师的老师)那样的大师也会后悔自己的少年之作。我们心中的楷模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流的大师,一心一意想走乾嘉考据学的路子,除了硬功夫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其他投机的路径可走。毕业答辩时由于只有一个人,文科师生很多都跑来听,地点选在可以全程录像的电教室,室内黑压压地拥满了人。时间则从下午2点折腾到五点半,根本就与现在有些高校一天就答辩二三十人不可同日而语。后来碰到前来助威的朋友,偶尔也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以为我答辩时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实则我浑身紧张、汗透衣衫。三年读书写了近百万字的东西,还惶恐得以为根本就没有进入学术的大门。
(注: 1975年,带学生去茶场认识植物。照片被贴在邮电大楼读报栏作为宣传照。)
大学本来是坚守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最高殿堂,但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已褪变成了产品加工厂。不仅论文、著作变成了可以用分值来计算考核的货物,甚至学生也成了可以用同样知识加工复制的产品。更严重的是学校变为行政衙门,依靠行政命令办学,根本就没有民主讨论的学风。学术不能高于政治,超越权力,反而受到政治的压抑,权力的捆绑,不仅学术本身难以繁荣,即人格精神也逐渐萎缩,伤害的不仅是正在成长的青年学生,而且更危及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
(注: 1978年,张新民和龚妮丽的结婚照。)
(注: 从乡下回城后当中学教师时,阅读线装书。)
学校的学风要由学术来体现,学术代表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学风是学术的外在感性显现,明显具有社会化特征。无论古今中外,学风都是社会的清流,即使古代动乱年代也少有例外。学风不能迎合或讨好世风,反而应引导或批判世风。学风好坏是国家好坏的晴雨表,集中体现了民族集体高层心灵的显意识。学风宁静淡定,世风再功利再浮躁,就像茫茫一片沙漠,仍有绿洲可供栖息。人格品性的成长发育是需要环境来配合的,学风和世风的醇正就是酿造美好人格品性的发酵剂。现在学风跟着世风一起坏掉,高校繁荣的背后深藏着危机。重建高校的学风,实际就是重建社会的希望,否则民族创造性的生机终会枯萎,国家刚健有力的气象必将窒息。
(注: 1982年,一家三代的合影。张新民父亲也是贵州大学历史系教师。)
5
其实,研究“清水江文书”是我意外闯进的一个学术领域。2002年调入贵州大学后,由于各种偶然的机缘,我才得知清水江流域遗存有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之丰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媲美,但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完全有可能散佚流失。或许出于内在不安难忍之情,或许来自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职业判断,便主动自觉地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保护,精力投入其中不知不觉已有十多年。好几位北京、上海的学界朋友批评我,说为什么要放弃原来已有成就的专长,去另起炉灶研究什么文书;我自己面对好几部写了一半就搁置的书稿,也真不免有些黯然神伤。好在我们洋洋22巨册的《天柱文书》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从中受益的海内学者人数已越来越多,十多年的心血精力似乎已有了补偿。前面说到“天命”的召唤就是最好的命运安排,其实“天命”的召唤就是心灵的召唤,我只能毫不犹豫地跟着它的呼唤向前走,一刻也不敢松懈怠惰。
民间契约文书是乡民社会生活的原始实录,乡土中国人际交往的文本大宗。每一份文书后面都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牵连家庭,关涉村落,合起来则为族群集体共同的记忆,显示了活生生的乡村文化历史。因而我称它们是“活”材料而非“死”材料,当然也是人类历史极为珍贵的民间记忆遗产。
如同考古学者发掘文物遗址,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必需的工作一样,研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表面看文书都很琐碎枯燥,但一旦从中了解到乡土中国的真实,梳理出乡土社会知识与价值的系谱,又会感到乐趣无穷。或许有人会问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呢?我想一方面要找到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散见的点联成有知识逻辑关系的线,然后又将线联成有完整人物故事的面;一方面则要开展田野调查,接触乡民活生生的故事记忆,将田野资料与文书资料互证互印,最后才能还原活生生的历史真实。这当然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学术工作,但与其他任何建设性的事业一样,前提仍是必须付出大量的心智劳作,远非互联网上轻松的点击可比。这当然并非认为不能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确也是了解社会风气变化的晴雨表。但网上的知识的确是碎片化的、即兴发挥而较少严密逻辑论证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信息。整天“泡”在里面只会使头脑简单,丧失了思考复杂社会人生问题的智慧能力。
任何学术工作都是一种艰辛严谨的劳作,必须形成完整系统的知识,当然就很难变成消费文字快速地传播。所以我经常告诫学生:甘于寂寞,守住边缘。一切消费的文字,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网络也好,微信也好,都像大海喧嚣的浪花一样,虽然光彩耀眼一时,却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仍会归于消歇沉寂。而严谨的学术或思想性的文字,静静地躺在大海的深处,并不像浪花那样汲汲于自我表暴,也不制造五光十色的幻象泡沫,尽管从来少人欣赏问津,却永远难以消逝毁灭。
上网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微信更能迅速有效地传播信息,我也尽可能地分享它的高效,当然不会反对它的存在。只是不愿意被它淹死,更不想讨好迎合大众,希望淡泊宁静地过好边缘化的人生。严格地说,信息可以摈弃,知识能够解构,只有智慧才与人生永远同在。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本体智慧,决非任何外部强力能够夺走。智慧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分享智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智慧的大门为每一个普通人敞开,它永远与人类的命运共在共存。
(注: 1988年,花溪公园里的一家三口。)
6
刚才提到学术成果如何为大众接受的问题,我的想法其实是区分层次和分别对待。譬如高深的学术就必须遵守高深学术的研究规律,通俗知识则有通俗知识的写作原则,娱乐文化又有娱乐文化的消遣方法,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不能“拉郎配”式地强行结婚,否则不仅生不出“宁馨儿”,反而会导致秩序的错位或紊乱,搞得各行各业一团糟。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本来就可以并行不悖,怕就怕非牛非马弄出个奇形怪胎。同样地,写正经历史就写正经历史,“正史”变成“戏说”只能令人看后喷饭;“八卦”“戏说”就是“八卦”“戏说”,僭越“正史”的美名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历史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就区分得很清楚,谁也不会将“正史”当“演义”,或者将“演义”当“正史”。二者都有不同的读者群,正好针对不同的社会阅读需要;譬如我少年时代好读《三国演义》,现在则更喜欢《三国志》,即使个人也有阅读需要的变化,根本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因为复杂历史的研究只是少数人才能从事的专业;但却可以要求人人都是艺术欣赏家,因为艺术作品的直观品鉴能力为每一个人所具有。就像刚才提到的清水江两岸的乡民,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家族村寨的生动故事,却未必就能研究自己的历史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品尝“戏说”历史的电视剧,却未必都能知道“戏说”背后固有的历史真实。但“戏说”毕竟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无论装进多少文学的“水分”,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而显得太荒唐太不靠谱。譬如让汉人穿唐装或唐人穿汉装,诸葛亮看线装书或朱元璋批竹简……闹出的笑话虽稍逊于让拿破仑穿马褂或康熙皇帝穿西装,到撒哈拉大沙漠去滑雪或到喜马拉雅山脉去找沙漠,但也出格得恍如看西洋镜,自己都变形得不是自己了。可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虽不是一回事,但也未必只会冲突不能统一,既能提供美感享受又能普及历史知识的影视历史剧,我想才是经典的传世的一流好作品。
(注: 1985年,张新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现场。)
(注: 1992年,在贵州地方志研究班做学术报告。)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本质上也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无论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大书深刻的“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抑或中国先秦老子所强调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都无不指明了人类自我了解和自我战胜的重要。但与动物永远都处于自然状况,只有自然演化史而无文化发展史不同,人从来都是历史中的人——在历史中创造,在历史中发明,在历史中发展,在历史中进步——历史充满了奇谲的变数,饱含着诡异的冲突,演绎了无数的悲欢离合,点缀了层出不尽的诗化作品,不仅研究对象远较有定律有规则的自然世界复杂,而且充满了无尽的妙乐真趣。历史幽深曲折的通道上堆满了认知的问题,问题的谱系链条逼着人一个个案接着一个案地探索,旧问题才解决新问题又迎面袭来,犹如“人在山阴道上行,美景目不暇接”,最终长时段变迁的历史真相会从大地的幽深处豁然现身,甚至现实世界的来龙去脉也会因历史的比照而显得一清二楚,当然就会有发现美洲新大陆般的兴奋。读史使人明智显然并非虚语,历史智慧的蓄积会使一个民族变得更加成熟。
(注: 2005年,张新民(左四)带的第一届贵州大学研究生毕业。)
历史的智慧当然也是一种时间的智慧。这里的时间虽然仍依托于纯粹自然的时间,但已有了人文化的历史意义,因而必须以人文化的方式来客观记年。人文化的时间积淀了人类无数的经验事实,充满了价值与意义,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合为一体。人有了丰富的历史感,就好像存在的时间空间都在扩大。无数古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已汇成一个连续的生命整体,有古有今长程变化发展的生命大流必然会使人活得更充实。屹立在历史文化上的一切生命,都因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关联而显得意义无穷。人如果只活在现实中,只有一个狭小的现实天地,人类历史完全萎缩为异己的存在,时间只有当下的即来即逝的意义,生命当然只会一片苍白,存在也毫无希望,人便会产生严重的异化问题,不能不退堕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意义上的“单面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那就尽量扩大领悟与体会的存在空间吧!
(注: 父女情深)
附1
内子龚妮丽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幼即随父亲学琴,音乐伴随了她的一生,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在童年时代便欣赏过她的“琴艺”,但最难忘的仍是在农村度过的无数冬夜,下乡的“知青”常常会围坐在火炉边,激烈地讨论各种“哲学”和“人生”问题。所谓问题其实都源自生命的痛苦和困惑,当然也渗透着青年人对未来的理想与期盼,只是更能给我们慰藉的仍非相互间的讨论,而是妮丽的琴声及其所开启的整个世界。所谓“仁言不如仁声入人之深”,旨哉斯言,旨哉斯言也!这样的生命境遇与体验,决非后来在音乐厅聆听正式的表演所能比拟。女儿婷婷继承“家学”,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不少与学琴有关的童年“趣谈”,但尽管如此,我仍预想不到女儿后来竟会醉心于被前人视为“小道”的古典戏曲,并立下了终身研究的职志。音乐营造了家庭的和谐氛围,表达了自由的致思,点缀了生活的美感,抒发了价值的渴求,不仅成为联结亲情的纽带,而且也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既是书本之外另一种切身的“学问”,也是我们最难忘最珍贵的情感记忆,其中的因缘故事甚多,决非短短的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认为传统审美经验的灵感活泉,乃是从事未来艺术创造最重要的资源。至于母女合作著述,亦为少见的文坛“佳话”。而我作为第一个读者,亦乐意为此“佳话”添加一些佐料,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留下一些有如眉批旁注的“评论”。
摘自 张新民为《乐韵中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龚妮丽 张婷婷/著)所作序言
附2
小舒大记者:
张老师二信均坚持称你大记者,既善意也很真诚,不是调侃一类之称。尧礼称您愚友,并非谦词,而是亲热,能列入“王痴人”愚友之列,你该高兴啊。我该称你什么呢?大手笔加小朋友吧。
你的提问,一次比一次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此语出于大人物)。这许多提问恐怕快成书了吗?不要急,还有更好的,一定能成为一本有小舒特色的高层次多领域纵横交错浑然一体的好书。你举重若轻,什么难题都敢碰,都能碰,拳头都轻轻砸在棉花上,精妙。
题目用“从古至今”极好,落在“痴人”上概括得好,与全文内容非常切合。是你把握全文精神的准确而有大气的表达力。
你说张老师也很会聊天。那是他一种炉火纯青的表现。他聊的小故事很好笑,传神,但也包涵妙理的通透感。
张先生回答仍很学术,但好懂,有些问题答得相当尖锐,是真话,甚至是诛心之论,看出张先生痴人不痴,是大明白人。对于他这样的大学问家,老夫不敢妄评,只能钦敬。
张先生的先君振佩公,1949年我听过多次他的历史公共课。四十年代就是中国研究《史通》的有数专家,他的《史通笺注》现为国内名著之一。张新民不愧是一代胜于一代。
上文是我边看报边写在边角上的,干脆抄录奉呈,算是老友的门外点赞吧。
学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