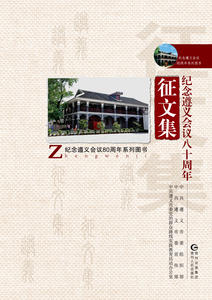目录
-
对遵义会议精神文化内涵的探讨
-
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论遵义会议精神中的军事民主及其当代价值
-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创造性推进群众路线思想建设的三个维度
-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
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期间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切实走好群众路线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是践行好群众路线的根本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增强党委议事决策能力
-
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机理探究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与思考
-
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作用
-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研究
-
论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对青少年的价值导向作用
-
刍议中央红军在黔北的扩红工作
-
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实党的群众路线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让群众路线永放光芒
-
“中国仡佬第一乡”的红军情结
-
由遵义会议“90字决议”谈贯彻群众路线改进文风的思考
-
浅谈“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启示与实践路径
-
遵义会议期间群众“幕后”拥军彰显民心向背
-
学好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
高擎遵义会议精神大纛 助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
由系列会议谈遵义会议精神
-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
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后勤供应工作
-
遵义会议透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因素
-
论“三人团”的分化瓦解与遵义会议的召开
-
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
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弘扬路径
-
遵义会议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
试论弘扬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
“四渡赤水文化”研究综述
-
遵义会议:中共和红军民主与团结建设的一个新起点
-
从遵义会议精神到群众路线教育
-
遵义会议前后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历史启迪
-
重大转折 全新起点
-
将坚持群众路线纳入新时期党员标准的思考
-
遵义会议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其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既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机,又面临着艰难的战略抉择。当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最紧迫任务就是解决红军的指挥权问题,让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称颂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恰如其分的。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正是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领导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
一
遵义会议以前,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是由于“我们党终究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的党。” [1] 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导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究其根源,从党内原因看,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还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规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2] 这表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征程中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就是由于共产国际“左”的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内事务的干预和包办所造成的。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成为国际性的事业,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出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但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主要应该依靠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革命,而不能靠任何国际组织来发号施令。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复杂原因,共产国际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遥控各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要求各国共产党绝对服从于、听命于这个中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崭新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在遵义会议以前又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几乎把中国革命拖入绝境。毛泽东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他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3] 1958年7月,毛泽东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在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 [4] 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当时出席会议的前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说:“中国共产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90%,党组织以及党在白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也遭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00被迫于1933年撤离上海,迁于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与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却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党的利益替代另一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方面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次谈话的内容和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自然是毛泽东早就思考过的。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再加上在军事上依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丢掉了南方的根据地而被迫进行长征。撤出中央苏区时,执行了逃跑主义,红军损失惨重,使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抉择。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他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5]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国情,在党内最早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6]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就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的主要对象,先后被剥夺了所兼的中央红军所有职务,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后来毛泽东说:“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重大损失,都是由于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所造成的后果。血的教训使广大干部战士开始清醒,他们纷纷要求变换领导,特别是原来跟着王明跑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经过毛泽东的帮助,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周恩来说:“在长征中,毛泽东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王稼祥也说:“在长征中,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转向毛泽东同志的决心。”伍修权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李德“排除在外”了 [7] 。李德曾经叹息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遇到的挫折,共产国际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是十分曲折复杂的,其实质是如何对待十月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他说,“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8] 这样,遵义会议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的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要服从它的领导。但是由于在此之前,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联系。这样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自己解决党内事务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最根本的是因为经过严重挫折,教育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深切认识到,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9]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
(一)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曾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革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这一时期,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通过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成功地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 [10] “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1]
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就在中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之下,经过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等人,逐步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大权。之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政治上贯彻和执行了一条更完备的“左”倾路线,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提出了武装保卫前苏联这一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从而失去了领导抗日民主运动的时机,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毛泽东说,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12] 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使中国革命再一次陷入危急之中。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从此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的统治,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
1.遵义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懂得独立自主
在遵义会议以前,具体地来讲,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共产国际这个因素,始终是挥之不去,能量巨大,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毛泽东深知王明之所以如此目中无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的理论水平,对中国革命有多大贡献,而只是因为有共产国际作他的后盾,具体来讲就是斯大林是他的靠山。毛泽东曾经说过:“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因此,能否解决“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关键就是要突破共产国际的藩篱,在排除共产国际这个因素的前提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由于遵义会议召开时,正像李德所说“完全同外界隔绝”,“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这样就避免了共产国际插手的问题。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组织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自己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作战指挥。特别是会议最终把“洋顾问”李德从“太上皇”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仅此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全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真正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说:“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前苏联一切都对,不把前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13]
2.会议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遵义会议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在中央苏区和遵义会议召开以前,毛泽东就同“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研究了开会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只讨论当时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出席会议的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这样,尽管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包括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作了检讨。凯丰反对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说毛泽东同志“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也多方为自己辩解,“更是完全的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14] 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多数同志通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和长征以来的损失,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长期的领导工作中,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经过正反对比,更加提高了毛泽东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崇高威信,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他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
3.会议正确处理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宣告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统治的终结,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尽管毛泽东等人十分清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由于全党的认识水平,特别是红军所处的严峻形势,如果会议专注于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很可能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中,甚至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后果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把军事问题作为主题,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干部战士看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由于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才使红军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因此,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样就保证了会议的成功。而且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措辞上,也没有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相互抵牾的地方。这虽然不符合中国党的实际,但在当时却易于一般的同志接受,既维护了党内团结,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15]
三
遵义会议尽管时间短暂,正式会议只有三天的时间,由于战事紧急,会议也是在晚上举行,但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愈加熠熠生辉,其突出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弥足珍贵。
(一)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革命遇到的挫折,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依靠某个外国或外国人决不会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可以说是一条真理。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说:“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16] “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 [17] 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革命中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有些还是直接违反了共产国际、前苏联的错误指示而形成的正确认识。仅仅依靠共产国际、前苏联写决议、定纲领、下指示,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总结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18] 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我们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建设事业得到了前苏联等国家的援助,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和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又提出,要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独立自主地搞建设,搞科学技术革命。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 依靠这条路线,使沉沦了100多年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位,引起世界瞩目。
(二)必须始终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20] 但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却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不懂得如何应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如果只是读了马列主义的书,而没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反而可能对革命造成损害。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的探索,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先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并且解释了它的具体含义。他说:“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一样。比如拿树来作比喻,一棵树同一棵树,它的根本一样,树叶总是不同的。杨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特点?总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杨柳,这一棵同那一棵总有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21]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22]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发生了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23] 这个进程将继续下去。
(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同样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鉴于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24] 敢于向权威挑战,不让僵死的教条捆住自己的手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自己的实践中,创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鲜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最可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遵义会议为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5]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0.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0,339,338~339,299~300.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5]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6~307.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10.
[7]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1~1949)[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82.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970.
[9] 毛泽东语,见《人民日报》1963年2月16日.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345.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345.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0,339,338~339,299~300.
[14] 《遵义会议文献》[M].人民出版社,1985:42.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970.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0,339,338~339,299~300.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0,339,338~339,299~300.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2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8.
[23]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N].光明日报,2011-07-2(2).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