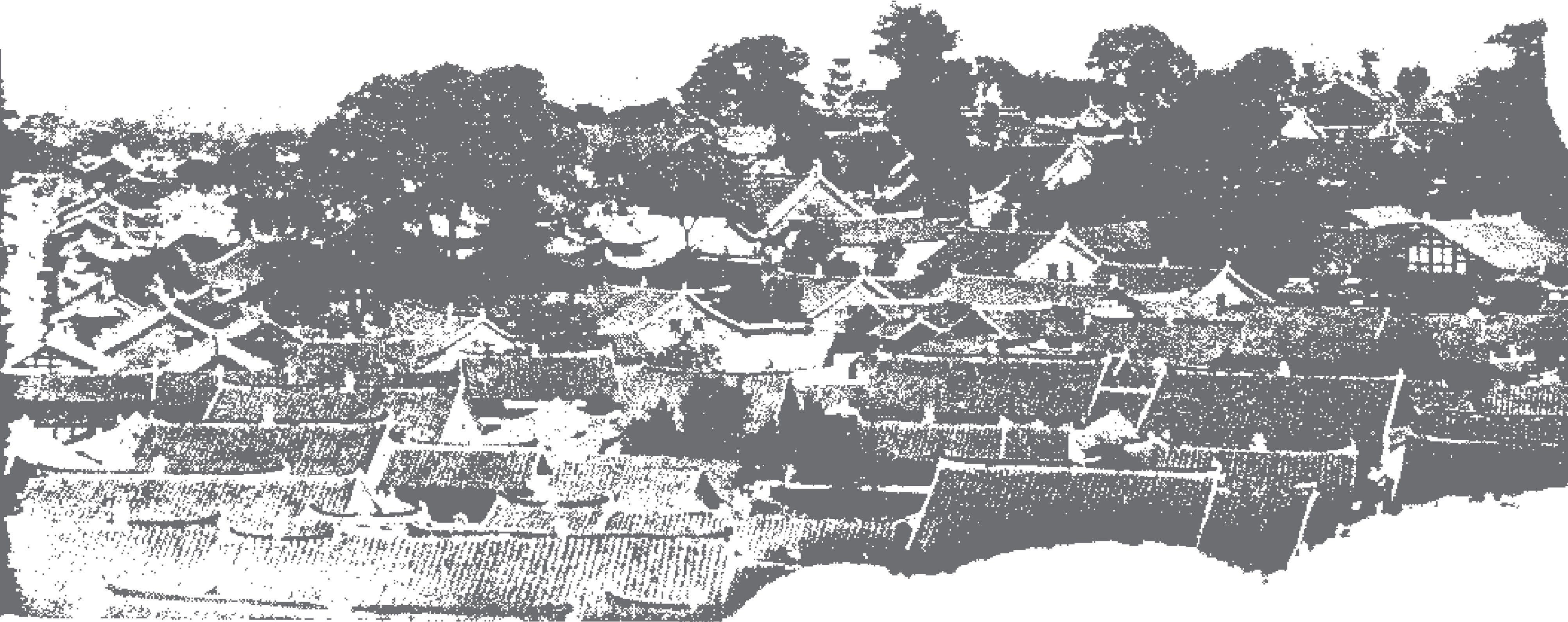目录
-
上编 文化名人看贵阳 [收起]
-
下编 文化名人与贵阳 [收起]
我的家庭和幼年
一九〇五年乙巳八月二十七日已时,我降生于贵阳大南门外太子坡(现名石岭街)我家旧宅中。
吾父名士瑞,号辑五,生于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幼年时代,已是家世衰败。在家塾里读过几年书,长得聪明俊秀。时清王朝已停止科举,没有了继承先人读书仕进的希望。父亲曾结识几位年龄相近的合心亲友,以文墨技艺相往来。这些亲友中有谭乃邦(是我的舅父),世家子,家富收藏,善扬琴;吴实夫,精音乐歌唱(入民国后为贵州著名作曲家,音乐教师);萧铁珊,工书法(为南京女书家萧娴之父),黄幼夫。
吾父于庚戌四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三十七岁。是年我五岁,我弟不满一岁,吾母三十四岁。母中年早寡,仅以吾父留下的十几间房屋,不盈二亩的园地经营,茹苦含辛,抚育我弟兄姐妹五人至于成立,吾母之恩,天高地厚矣。
几十年来,我犹及依稀想到梦到我父在时和他去世之后家中的许多情景,常感慨唏嘘,不能自已。
一九二五年谢孝思(中)青年时代与弟兄在贵阳石岭街老宅
我家住大南门外半乡半城的太子坡(现名石岭街)。屋前是南门外乡下人进城必经的石块路。原来我父家庭中落以后,把分得的十几亩祖遗田产,变卖得了几百两银子,因外祖父谭溁波的主张,在隔他老人家住宅不过二百步的地方,买了一块五、六亩的地皮。我父虽然读书不多,却情趣风雅。就在这块地皮上,布置得相当雅致,街坊上称为“谢家花园”。
庭院一区,东边建三间平屋,前半临街为双合铺。左边为我父经营的酒店,兼卖盐米杂货(贵阳叫盐米铺)。我父好饮酒,慕陶渊明之为人,取招牌曰“醉陶山庄”;右边为我满姨父胡月之所开的布店,招牌曰“虔信字号”。这两面招牌大字都是萧铁珊所书。书法刘石庵,丰美可爱。两铺面中间,右边柜台侧,放长条板凳一张,供吃柜台酒的乡民所坐。屋的后半为坐家。中间堂屋大门两侧板壁上,有精工的平雕钟鼎博古。忆我母曾告诉我弟兄,此系萧铁珊书写,吾父雕刻的。这三间房屋,在吾父去世之前年,即都为我满姨父所住,酒店也顶给他经营了。
我父先开酒店,后来又与熊华堂,朱铁匠(邻近太子坡迎恩寺以打铁起家的老者,他的三个儿子和我弟兄曾是私塾中的同学)合伙在倒岩、猴场坝开了两座瓦窑。家中后院草房养了几匹马供运输。因此赚了千把两银子。于是在原来三间平房的右首,远对南岳山处,建了一栋有三级台阶、长三间砖墙楼房。原来的三间平房便成了厢房了。房前一石板大院,院之西有苦竹林二丛数百竿面对厢房。近正房的廊杆前竹林中藏麻雀盈千百,清早大噪而飞出,傍晚归林亦大噪,为吾家的“计时钟”。院中正房近左檐下有紫薇一树,我弟兄幼时常攀上嬉戏。院北有梨树一株,粗不过碗大,闻年纪已三四十岁。连年花开甚繁,而结果不过十数只。我母严戒不许偷摘,待八、九月之际透熟,每只长到斤重,才由我母分送外公、姨父,大家共食之,有的还留以待至亲长辈。院坝南边一排放置十几个高约三尺的石磴,上置径二、三尺的大花钵,中植梨子、花红、羊奶等开花结果的植物。这些都是吾父手中所置或亲手所植者。院坝坎下皆土地。北面牖壁上塑“一团和气”图,其下有花台一座,中置一木假山,满长青苔、虎耳草,两旁植牡丹数株,但从不见开花,后来竟被人偷挖去了。花台下置石桌石凳,我父常在此与酒友或乡下农民吃酒。也有经常来店的酒客光顾此处。花坛左植芭蕉一丛,右栽樱桃一树,前植白石榴一株,花果皆白。远近邻居有患耳脓者,我母亲常以小竹筒削成斜口插入焦茎中,接汁以治之,有特效。
竹林后面,有六角茅草亭一座,两面有栏杆可坐。中设板床,上悬横匾,篆书“不亦快哉”,有跋语本苏子由《快哉亭记》大意,寄吾父情怀。亭前两柱悬行书对“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皆萧铁珊书。亭左有老石榴一株斜倚亭簷,开花甚繁,果酸。以老树可爱,吾母禁伐之。亭前左右及花台一带土地上,吾父在时,广种菊花。闻吾母言,每菊花盛开,远近街邻及亲友,乡下路过村民来观赏者不绝。厢房右侧低下一台阶,建屋一间,面前开月宫门,上有横匾,绿底黑字楷书“悠然见南山”,后有吾父跋语:“此靖节先生句也,先生晋之隐士,高风千古,仆也不才,心向往之,爰辟小园,面对南山,……录先生之句,慕先生之风,聊以自娱云耳。□年□月辑五氏”。又有一副木刻玉箸篆对联,已忘挂在何处,后我弟兄在楼上检出,挂在正房厅口柱上。文曰:“杂花装林,碧草盖地;高朋满座,旨酒盈樽。”以上这些匾对皆吾父至交萧铁珊册书。吾兄弟遵母命谨心保护。尔时,虽于其中文章倒懂不懂,却欣爱之。
曾闻母言,铁珊先生与吾父交情甚厚,曾许下为儿女亲家。萧女与吾兄盖年相若也。不知隔了几年,萧先生携家离开贵阳,后若干年闻他家去了广东。虽然这是一段未成的姻缘,萧女娴在南京成了名书家,但足见谢、萧两家的情深。
亭后筑土墙一带转角与正房右边的砖墙相连,中开圆顶小门,贴正房砖墙盖三间小屋,前面围墙另成一小园地,中间凿池塘,不方不圆,现出石岩小岛,颇有天然情趣。小屋曾供作街坊私塾之所,曾记得吾兄和朱铁匠家儿子等十几个学童在焉。老师姓张,颈后有隆起肉包,大家背后叫他张包包。吾父死后,亲友中相地者,谓房头破土凿地伤了地脉,不祥,遂填平了池塘。
由小院通门到后园,园大盈二亩。中间所植果木成林。大都是吾父购置此地时前人种下者,其中最高大的一株鸡爪,合抱大,殆数十年物。杏子二株,柑子、花红一二十株,多老干新枝,年年开花结实。花果树下种青菜,辣菜,不用浇粪肥而长得肥大。犹记得我六七岁时,在春天杏花开时,花瓣纷纷落在肥大的青菜叶上,我和住在园子南边草房里(当年养马的草房,吾母改成住家以出租者)一家姓萧的女孩儿,搀着手到杏花树下,我牵着衣兜,她在青菜叶上拾取片片的落花放在我的衣兜里。这种情景,几十年来,还常常在梦中出现。
园中花红是清镇的佳种,和柑子十馀株,半年开花,果实皆硕大而甘美。老干枯萎,根下长出新枝,吾母教我弟兄姐妹壅土盖上根际,隔年生了须根,掰取移植后,不几年皆开花结果。我长到十来岁时,园中花红、柑子树正是子树繁茂的时期,加上草亭侧边所种的葡萄,都结实累累。收可数十百斤。除少数自家吃和赠送至亲外,大部卖给果商,以助家庭生活。
吾母治家谨严,更利用园中采菜和每天的淘米水,在草房侧边盖了个猪圈。每年养两头猪。这是吾姐文琴和佣女的任务。我家先后有贵香、秋红、来顺三个女佣,她们都是最贫穷人家的儿女,为我家付出大量劳动。我母亲厚道,严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许虐待她们。贵香长大到二十岁时许配给她所喜爱的农家子弟,每年收获后他俩还到我家作客。秋红十三岁患天花死,全家哭之哀,葬她于吾前母墓地,年年同祭扫。来顺嫁到抗战后我家迁居的农家寨姓熊的人家,今犹在,近年我还乡去看望过她。
吾母不识字。她每每对我们儿女谈到,谢家世代书香,儿子要好好读书,不辱先人家风。所以对我弟兄读书识字管教严格,而于我姐我妹则委之家务。吾姐从未入学,吾妹只读过两年的小学而止了,进的是近家不远办在雷祖庙前一个较落后的兰因小学。
我六岁时,母亲送我到迎恩寺对面胡先生(忘其名,街坊上都叫他“胡幺幺”)私塾发蒙。这间书房,前临街道,后面是靠在石崖上的吊脚楼,面临杨家大河。吾兄和朱铁匠家两弟兄福全、福元以及近街坊乡间的学生十馀人。胡先生瘦削个子,相貌严肃,从不见有笑容。他用土红笔教我《三字经》。我垫高脚尖才能勉强看到他的教桌上摊的课本。有一天,我立在桌边听胡先生教识字的时候,小便甚急,又不敢告诉他,小便便忍不住顺着裤子淌了下来。我偷偷俯看下瞧。胡先生发觉了,鼓起眼睛对我说:“你这个娃娃,赶快去屙了来!”我愈加怕他。第二天不敢去上学了。后来是我母亲又亲自送我去。读了一年,胡先生患病,私塾停了。我和我兄一起进入马棚街王公祠第五模范初等小学(这所公立的模范小学,高等小学部设在城内大坝子,下有五个初等小学。王公祠所在南门城外,名列最后,其馀皆在城内。祠内有明建石亭碑刻)。我兄入四年级,我入二年级。一位肥胖的国文老师黄先生和一位穿短服教体操、音乐的胡先生。我很喜爱听他的课,曾忆黄先生有一次出一个嵌字题“……甚……”,我的答案是“中秋食月饼甚香”。黄先生发下作文本时向我笑个不停,我莫名其妙。缘由才过了中秋节,是我这个小孩儿最深的感受。
次年我兄升入城中大坝子(距吾家五、六里)模范高等小学。吾母不放心我每天上下午不能与兄一道来回;又因外祖父的主张,改进迎恩寺坎下铁匠街(又名粑粑街)陈满公(忘其名)家塾。陈先生是前清秀才,近视眼,大胡子,住家土墙小院。院边种苦竹石榴。住房正对陈家坡,远望南岳山,这在街坊上算得一处幽雅的院子。我们的书房就在陈先生的堂屋里。同学十七八人。我和私馆对门陈铁匠家儿子陈应铨最相好,经常一起游玩。课前课后到迎恩寺里打抛(是自己用棉花以青白线扎成的绣球),有时到陈家坡、南岳山脚挑野花野菜,也曾在深秋梧桐果熟时,到几里外东门螺丝山阳明祠游玩、拣梧桐子,也曾和他一道编《诗经字典》(把《诗经》里的难认字录成不盈三寸的小册子)。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应铨在陈家坡上挑苦蒜,恰被我姐下乡路过发现,她回家禀告母亲。母亲叫我跪下,拿取鸡毛帚把棍在我股下狠打了几下,训我不许浪游逃学。
提起这鸡毛帚棍子,可算是我母管教我的“好朋友”。我自从发蒙上学以后,由于家境不宽裕,没有钟表。一家人每天都是看太阳照在厅口墙壁上的高低和早晚竹林中麻雀出入噪声来观测时间。我幼时早晨瞌睡多,醒不过来,该起床时,母亲叫了我一次,我哼了一声,又睡去了;我母叫了我三次,我还不起床,她老便拿着鸡毛帚,揭开被盖,在我屁股上狠狠相交了三几下,我惊痛大叫,便翻葫芦爬起来,赶紧洗脸抱书包上学。
我在陈家私塾读了三年。从《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诗经》《书经》,这些书都分别背过多少遍,但陈先生从未讲过。我虽然不懂中间讲的什么内容,由于记忆力强,并不大觉得费力而容易成诵。所以我从来不曾因为背诵不出而挨过“手板”(二尺的竹板,以责手心),是陈先生几次所夸奖的学生。第三年读《小学集解》,这部书中记载了一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和格言,虽然先生没有讲解,我多少明白了些儿,特别感到兴味。对中间的一些人物故事,产生了敬仰的感情。
二十世纪初贵阳城一角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陈先生开始教作对联。我虽然没有读过《声律合蒙》,但听年长的同学读多遍了,也记得一些,所以也逐渐能属四个字的联语。
一九一六年,我十一岁,我的舅父杨仲森租住我家月洞门厢房。他很关心我们弟兄的培养。他向我母亲建议,不要我再读私塾。得我母亲和外祖父的同意,在他的介绍下,我和三弟孝慈进了正谊小学。我进高等小学一年级,我弟入初小一年级。他时年七岁。
正谊小学距我家约三里。时我兄进火药局模范中学。两校相距不远,每天早晨三弟兄买三文钱的糍粑同路上学,上下午来回四趟。天雨少伞,湿透布鞋操衣制服(只有一套),只得回家现洗现炕,都是我姐和我们自己料理。
正谊小学管教严格。我和三弟都能恪守校规,用功学习,得到各位老师的嘉许。我初进正谊时,人地生疏,拘局寡偶,只认识同班同学叶汝昕、陈时乾。我在功课上最害怕上算术课,因读了三年私塾,加减乘除全无根底,而班上的算术老师都是监学先生。严厉非常的傅少华先生,一开始教的便是“四则杂题”,每一题还需作解。曾记得开始第一课题为:“大小二数和、差为若干,求二数”,第二课为:“鸡兔同笼,头、足数为若干,求鸡兔数。”我真莫名其妙。我只得照抄,苦苦用功两三月,才勉强赶上。记得第一个学期考试算术的早晨,忧愁非常,临近上课,大便甚急。入厕后匆匆起来,所遗大便全装在裤裆里,两手急忙抓出赶到教室,弄得满室臭气,大家不知从何而来。所幸题目不深,大体都答对了。
国文先生龙仲衡,也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他讲课字字清楚,虚字都解得明白。我感到深切有味。他每课都要考学生背诵讲答,不能背诵对答的予以斥责乃至打耳光。我则背诵讲答都能做到,得他的奖评。那时的教材都是文言文,作文也须用文言文作。我进正谊前从未用文言作文。我记得龙先生开始第一次作文题目是“勤学说”,两个钟头的作文时间。我的一篇文章是:“人生在世,必须勤学;若不勤学则不能成人矣。”龙先生的批语是:“尚顺,欠发挥。”龙先生教习字,他写的一笔颜鲁公很有功夫。每课用毛笔醮着铅粉大书四至六个字在黑板上,教学生临摹。我非常喜欢他的字,逐渐临得很像。我的习字本中几乎每字都得“○”,有的还得“ ”。龙先生又常叫我上讲台肖他用铅粉大书。我能写得有些相像时,他就微笑点头。龙先生曾自己花钱,买了颜真卿、翁同龢的字帖奖励我,我非常感激,在家临摹。龙先生可算是我的文学书法的奠基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学期的考试,我名列第六,列第一名的是王玉光;自第二学期,我便名列第一了。我弟孝慈聪明过人,他自初一级直到六年级毕业一直名列第一。那时老师们常常夸说“谢家两弟兄”。
我是老师们称许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二年级后任级长,都受表扬。只有一次在高二级下学期考试的时候,那时龙仲衡先生考进了邮政局工作,学校由田光(老胡子)先生代课。而田先生未亲临主考,却由校长廖勤九将他的出题《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论》写在黑板上,命同学们做好后由我收集考卷送校长室。廖先生离开后,全级同学静默了一阵,接着骚动起来,这个题目讲不动,难得做,做不出,嚷成一片,首先就有一位同学大声提出:“交白卷!”接着又一位同学大声附和道:“不交白卷的是屁娃娃!”紧接着,班上身材最高大的何为贵高声表示:“老子来收!”于是,他挨座收取大家空白的考卷放在讲台上。这段时间,我莫可如何,只得听大家的行动。下课时间到了,校长廖勤九先生来到,见着这个局面,问了我大致的情况,于是叫我和刚才领头的几个同学到教员憩息室里。当时在室内的还有陈寿轩、喻小泉两位先生,三位先生一致认为这事故非常严重。首先叫我谈了经过情况,接着廖先生叫何为贵抬了板凳来,将几个主张交白卷的同学一一打了二十至三十板屁股。最后谈到我,廖先生似乎温和一些,陈先生则在侧边说了一句“其心可诛”,于是三位先生一致同意责我二十板屁股。真痛呀!我叫喊起来,惭愧害羞。回到家中,不敢露半点声色给母亲和家人知道。这次学期考试,我仍然名列第一。
这时,我的家境愈更贫穷,已难支持我入学。恰当我兄从模范中学毕业,与龙先生同榜考取了“邮务生”,每月有十几元工资。于是全家欢喜。因此,我得与三弟继续入校学习。
一九二零年,我从正谊小学毕业。本来准备投考师范学校,以毕业后能当小学教师有生活保证。因见报载达德学校开办中学,用白话文招生的广告,我感到新奇,于是考入了达德中学。
我自幼喜爱绘画。我家曾祖父谢宝书的自画“桐阴消夏图轴”和扇面等引起我弟兄对绘画的爱好。我在正谊小学时的图画教师贾仲民先生,我在中学时的图画教师马啸澄先生,是使我产生对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的认识和热爱,以至作为终身事业的恩师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