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布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摩经
摩经,即摩教经典,布依语称“诗摩”[sɯ1mo1],摩经是布依族宗教祭司布摩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念诵的经文的总称,是布依族传统宗教之所以被认定为准人为宗教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摩教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
(一)摩经的类别与主要经卷
摩经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根据适用范围,可分为“殡亡经”、傩书和“邦经”(或称“改邦经”)三大系统。“殡亡经”用于丧葬仪式,傩书是傩仪上所用的经文和傩戏脚本,“改邦经”用于驱邪、祈福仪式。
“殡亡”[pjaŋ3fa:ŋ2],是布依语第一土语区对丧葬仪式活动的称谓。在第二土语区,称为“砍牛”,第三土语区则称为“古谢亡”、“古夜亡”(意为“做鬼客”)。因此,殡亡经在第二土语区和第三土语区被分别称为“砍牛经”和“古谢经”。
目前,在贵州、云南布依族分布地区的三个土语区中,均发现有摩经传承,其中,傩书只在贵州荔波一带发现。由于摩经只有少量得到翻译整理和出版,因此,摩经到底有多少卷册,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统计过。根据已公开出版、内部印行和笔者调查的情况,主要有以下篇目:
1.殡亡经
(1)流行于贵州镇宁一带的《古谢经》,收录经文七卷:
第一卷《穆考》(头经);
第二卷《穆告》(魂竿经);
第三卷《穆翁》(坝场经);
第四卷《穆荡》(嘱咐经);
第五卷《穆近》(转场经,包括构荣、构兜、仲欢、构睐、坝兜埃止、构地、那外、构盆、构养、构马、构领、构督、构半远、构丹、构正、构厌补韦等16节);
第六卷《穆揆》(婿祭经);
第七卷《穆稳》(咒牛经)。
(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六十五集收录花溪把火寨摩经共十二卷:
第一卷《送食经》;
第二卷《送衣裙经》;
第三卷《请师经》;
第四卷《起首经》;
第五卷《造房经》;
第六卷《牛经》;
第七卷《嘱咐经》;
第八卷《请土地经》;
第九卷《送乌鸦经》;
第十卷《解陷塌经》;
第十一卷《嘱马经》;
第十二卷《分花树经》。
(3)《民间文学资料》六十四集收录贞丰县者相镇一带《丧葬歌》共五卷:
第一卷《赶嘎经》(共27节);
第二卷《招魂歌》(即《汗王与梭王》);
第三卷《婿祭歌》;
第四卷《请魂歌》(共13节);
第五卷《出丧歌》。
(4)已公开出版的殡亡经:
《安王与祖王》;
《母祝文》;
《摩当——布依嘱咐经》;
《温经》;
《布依族古歌》(部分作品)。
(5)笔者自1986年至今调查搜集存目未印刷出版的部分摩经:
A.罗甸的《殡亡经》有:
a.《转粑槽经》;
b.《写字(幡文)经》;
c.《牛歌》;
d.《牛经》;
e.《女婿祭经》;
f.《孝男孝女祭经》;
g.《嘱咐经》;
B.望谟的《殡亡经》有:
a.《绕棺经》;
b.《嘱咐亡灵经》;
c.《登仙(天)经》;
d.《孝男孝女祭经》;
C.云南省罗平县多衣村的《殡亡经》有:
a.《梳头经》;
b.《打粑槽经》;
c.《解灾经》;
d.《书(幡文)经》;
e.《下场经》;
f.《转场经》;
g.《起首经》》;
h.《万(歌)经》([mo1van1],共三类:《报信》、《老(大)歌》、《光棍孤独歌》);
i.《孝男孝女祭经》;
j.《乌鸦经》;
k.《嘱咐经》。
D.贞丰县北盘江镇岜浩村的《殡亡经》。这套经书最多,计十五卷,它们是:
a.《祭棺经》;
b.《入冥经》;
c.《出冥经》;
d.《温(歌)经》(共十三节,即《呼唤歌》、《病痛歌》、《报姑爷歌》、《建家歌》、《穷困孤独歌》、《宵夜歌》、《送仙歌》、《丑听歌》、《猜歌》、《兴情侣歌》、《逃婚歌》、《贬抑歌》、《分离歌》);
e.《祭幡经》;
f.《挂幡经》;
g.《祭祀经》;
h.《长寿经》》;
i.《下场经》(共24节,即《建家》、《造窝》、《造门》、《造梯坎》、《造神》、《出院门》、《造坟地》、《祭场地》、《画》、《送乌鸦》、《颖之歌》、《造牛》、《造马刀》、《赞马刀》、《捆牛》、《私房牛》、《孝子孝女禁食砍嘎牛》、《屠牛》、《兴起转动》、《寻种》等);
j.《上棺旁经》;
k.《孝子祭经》;
l.《女婿祭经》;
m.《嘱咐经》;
n.《赎谷魂经》;
o.《赎头经》(或《告王》)。
各地经文数量不同,有各种原因,一是在一些地区,有的经卷已经失传,有的则把不同经卷合并到某个名目里。各地经文有些名称相同,有些虽名称不尽相同,但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名称完全相同,内容也有一定差异。这与摩教还未发展为成熟的人为宗教有关。但这些同与不同,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2.傩书
傩书是傩仪上所用的经文和傩戏表演的脚本。目前只在荔波发现有傩书。从2010年起,荔波有关部门开始申报珍贵古籍文献,先后三批,有16本列入国家珍贵古籍文献目录:
第二批:《献酒备用》、《解书神庙》、《汉皇书》、《关煞向书注解》、《接魂大全》;
第三批:《掌诀》、《修桥补路》、《架桥还愿》、《罢筵倒坛》、《祭祀请神》、《傩愿问答》;
第四批:《祈请婆王》、《盘古前皇》、《祭解全卷大小通用》、《巨鹿氏》、《做桥》。
3.邦经(改邦经)
邦经,巫的色彩更浓一些。邦经是“改邦”仪式上吟诵的经文。“改”,布依语发音为[ka:i3],有“禳解”之意;“邦”,布依语发音为[pa:ŋ1],多为邪恶鬼怪,也有部分正神,只要“邦”作祟于人,使人得病,或做事不顺,都需要举行“改邦”仪式,予以禳解,才会得到改善。
目前搜集整理印行或存目的有《请龙歌》、《接龙经》、《擒雕歌》、《六月六祭词》、《访几经》、《退仙经》、《扫寨经》、《请祖宗经》、《祭母神经》、《保福经》等等,每一种驱邪祛病祈福的仪式也有相应经文。每种仪式的经文往往还包含多卷本,如荔波一带用于祧祭的傩经就有《开坛歌》、《请神歌》、《唱诸神》、《献茶献酒歌》、《送花歌》、《古老歌》、《十二花王歌》、《撤坛歌》、《古摩古改歌》等等。与殡亡经篇幅一般较长的情况不同,改邦经的篇幅一般较短。因涉及的方面多,此类经文也被称为“杂经”。
(二)摩经的主要内容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摩经主要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
一是祈祷词。作为宗教仪式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文,祈祷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最为基本和原始的构成因素。这是因为无论是祈求型的还是驱逐祓除型的仪式都有具体的对象,而且有相应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必然就有祈求,有祷告。在很多仪式开始时,摩经都要念诵这么几句固定经文:
接下来是说供奉了哪些牺牲,请对方享用后做什么,等等。
二是远古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的则只有一些残片。例如荔波一带的摩经《人寿传说》对人寿如何由长到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叙说,有较为完整的情节。流行于很多地方的有关射日和洪水神话也有完整情节。有些神话传说有故事情节,但却不完整,只是一个故事片段。例如贞丰、望谟等地摩经中关于房屋起源和发展演变的传说就是这样。它不像《安王与祖王》那样,一部经文就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情节完整的故事,而是在整部经文中,插入了一段虽有情节但却首尾不完整的故事。
在很多情况下,远古神话传说只出现一些残片,如贞丰摩经《转场经》中的一段:
这里,虽缺乏完整情节的叙述,但布依族民间和摩经中均有关于远古时十二个太阳并出,晒死庄稼、植物和人的神话,显然,这几句是引述而来。如果民间或摩经中已经没有了相关的作品,这样一些残片就十分难以理解了,成了没有出处的死“典故”。摩经中有诸多此类情况。也有一些作品,在某些地区无论经文中还是民间,都还传承着,而在一些地区,民间还有传说,但经文中只有“残片”了。如有关“颍”([viŋ4])的传说即如此。相传,远古时候,人死后邻人分而食之。后来“颍”不忍心让人吃自己亲人的肉,故以牛代之,形成了丧葬仪式上砍牛的习俗。 [1] 民间传说流行很普遍,但摩经中,只有望谟、罗甸、荔波、平塘等地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而在其他地区的摩经中只保留了一些片段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民间传说流传在先,后来一些地区的布摩将其适当改造后吸收进了摩经中,有的地区的布摩则只将作品的片段吸收进摩经。
三是故事。故事和神话传说都有情节,但神话传说比起故事来,幻想性和传奇色彩更浓,而故事则只是叙述一件事情。例如各地经文中都有请木匠师傅来制棺木,请布摩前来超度亡灵的故事,上山伐木制棺的故事,请“押”(巫)来为死者招魂的故事和采伐竹子作幡竿的故事,到死者女儿女婿家报丧的故事,请阴阳先生来采风水宝地的故事等等。这些所谓“故事”,实际上人物关系非常简单,情节也非常单纯,并且常使用相同的叙述模式。例如采伐竹子作幡竿、找好木料伐木制作棺材等故事,都没有交代具体人物,而在叙述采伐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经过严格选择,或十棵或十二棵,第一棵是什么情况,不要,第二棵是什么情况,也不要……一直选到第十棵或第十二棵,找到满意的竹子或树木后,才砍伐。之后又叙述怎么砍,怎么修枝,怎么搬运回家,怎么请来匠人,匠人怎么制作,制作好的棺木如何精致,装水不会漏,告诫亡灵不要卖掉,要留着作为遮风避雨的住所等等。而在请木匠制棺、请“押”为死者招魂、请阴阳先生采地、到女婿家报丧等“故事”中,去请或去报丧者均是两个小伙子,当两小伙到达后,主人都无一例外这样发问:一年到头不见你们来,你们眉头紧锁、阴沉着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该不是被人抢了或与别人发生纠纷了?而两个小伙也无一例外都作了否定回答,之后,如实告知来意,如此等等。
四是长篇叙事性作品。比较著名的有叙述历史故事的《安王与祖王》(或译《罕温与索温》、《岸王与梭王》等),此外,荔波一带以求子保子为目的的傩仪经文中有爱情叙事歌《范龙》、《范朗与媚香》、《马赛》等等。《范龙》在望谟、贞丰等地民间是以民间长诗或民间说唱的形式流传,布依族诗人毛鹰和几位布依族文化工作者搜集流行于望谟的作品并加以整理后以《金竹情》为篇名公开发表于《南风》杂志。在安龙一带,本篇作品则早被改编成布依戏剧目《胡喜和南洋》。
五是抒情类作品。贵州省贞丰一带和云南省罗平一带的《温》是比较典型的抒情作品。除此之外,各地经文中的《送仙》、《登仙》、《嘱咐》等,也有浓重的抒情风格。经文中布摩、死者亲人对亡灵的诉说,或亡灵与阳世亲人之间的相互嘱咐,都反映出一种悲悯的或眷念的情怀。
(三)摩经:布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摩经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资料,尽管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但通过文献、考古、民族志、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方法,可以梳理出布依族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和各历史时期文化的基本面貌。摩经是布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摩经虽有一定程度的变异性,但由于其宗教经典的特殊性质,同一般民间口头文学相比,其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摩经中反映的布依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不因大幅度的变异而丧失本来的面目。布依族历史上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缺乏文献资料,而汉文史料记载又语焉不详且多有歪曲不实之词,摩经更显示出了它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它为我们研究布依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布依族的民族特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人们活动的轨迹。而人们活动的结果表现为文化的创造和传承。因此,历史与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是同一个含义。尤其像摩经这样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的特殊文献,我们只能根据其中的材料,通过归纳、分析,描述文化面貌,梳理历史发展脉络。
布依族文化涉及的面很广,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1.摩经反映的布依族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和物质生活文化。
物质生产文化,指与物质生产活动相关的文化。摩经中,对布依族物质生产文化有诸多反映。
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古代布依族地区,森林茂密,野兽出没,野生植物和水果非常丰富,为狩猎和采集提供了良好条件;傍水而居,正好有捕鱼之便。摩经中的射日和洪水神话,有“比香”(或“老姜”)制造弓箭射杀太阳的情节,很多经卷中有关捕鱼生活、鱼名、鱼网等的记述,以及有关食物或祭品如蕨菜、冬兰菜、竹笋、芭蕉、野芭蕉等的诸多记述,无疑都是布依族早期狩猎、捕鱼和采集生活的反映。
世界各民族在最初一般都经过渔猎和采集生活的阶段。新石器时代开始,各民族先民的发展道路由于不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分别向畜牧、捕鱼或农耕发展,在以其中某种行业(畜牧、渔猎、农耕)为主的人们共同体那里,其余行业就变成了一种作为补充形式的副业存在着。在布依族中,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采集逐步向农耕发展,渔业以及野生植物的采集退居次要地位。这一转变发生得比较早,以至在摩经中的《射日·洪水》神话以及古史歌《安王与祖王》等早期作品中,这一特点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
古百越是最早驯化野生稻、发明水稻种植的民族(李昆生)。 [2] 以布依语、壮语“纳”[na2](田)、“峒”[toŋ6](坝子)为词头的地名,就是古越人从事稻作农耕的重要标志。有学者根据云南发现野生稻最多的事实推测,云南可能是最先驯化野生稻、发明稻谷栽培技术的地方。 [3] 贵州与云南具有相同环境条件,“还一向被有些农学家视为水稻的起源地之一” [4] 。
近年来,考古学家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究中心韩斌课题组完成的研究显示,人类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为广西。2012年10月3日的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发表黄学辉等人《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的文章,作者通过基因分析,推断水稻驯化后的扩散路径为:人类祖先在珠江流域利用当地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粳稻,随后往北逐渐扩散。往南扩散中的一支进入了东南亚,在当地与野生稻杂交,经历了第二次驯化,产生了籼稻。南北盘江属于珠江水系,是布依族分布的腹地,考古工作者在布依族分布的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发掘了稻谷遗存,充分说明了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的越人参与了人工稻驯化,是人工稻栽培技术的发明者。
布依族是百越中骆越后裔之一,稻作农耕文化具有悠久历史。摩经中反映出的以稻谷的种植为其突出内容的农耕文化,就是百越稻作文化的突出反映,为百越最早从事稻作农耕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摩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稻谷的耕作不仅很早就进入了犁耕阶段,而且派生出一系列关于水稻的文化因素。综观摩经,我们对布依族农耕的特性获得的是一种强烈的“稻作文化”的印象。
《安王与祖王》中叙述祖王出生前后安王所受待遇的变化时说:未生祖王时,“祖宗田”、“肥沃田”、“井边田”、“水母田”、“水挲牛(幼小的牝水牛)”都给安王;生下祖王后,这些都不给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很难保证收成的田,“天干给望天田,涨水给窝凼田”。很显然,作品反映的是比较进步的稻作犁耕农业。分给水牛,正好说明所反映的时代已使用犁耕。在《射日·洪水》中,就更直接地反映稻作农耕了。“王”之所以诏天下人射日,是因为天旱种不出粮食;“王”用作射日的报偿是好田;“王”食言后,射日者用蛇作纤索,套上狗犁田;洪水过后寻谷种重新耕种……作品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即稻谷的耕作。用猪狗犁田的情节正是犁耕农业的反映。在黔西南兴仁、兴义一带,布依族过六月六时要举行“扫坝”仪式,由布摩带领一队青壮年男子,拉着一只或几只狗,在长满禾苗的田坝间巡游,举行驱虫或驱疫仪式,布摩一边走一边念诵《驱虫经》或《驱疫经》,之后集体会餐。初六、初七两天内不准任何人到田里干活,违规者,过去要罚款重祭,再罚修路一段。这一仪式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驱虫或驱疫,使粮食不受虫灾,获得丰收。无论是仪式本身还是经文,都直接反映了布依族的稻作文化。
摩经中的这一记载与一些汉文献的记载考古地下发掘相吻合。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西南夷的社会生产状况时说他们“耕田,有邑聚”。 [5] 西南夷中包括布依族先民。能比较有力地证明布依族稻作文化的考古发掘当推云南元谋大石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三千年的稻谷粉末。该地附近有含“那”的地名上那蚌村和大那乌。“那”在布依语中意为“田”。根据地名学的一般原理,含“那”的地名一般应来源于水稻的栽培。 [6] 因此,可以推知布依族先民很早的时候就在这一带从事稻作农耕了。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的约七千年前的谷物遗存,也是百越很早就开始从事稻作农耕的反映。在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稻谷遗存,说明贵州高原古人类也是最早从事稻谷栽培的人群。这些古人类,自然包括了布依族先民。
物质生产方面还有对冶炼与铜鼓铸造的记载等,都是研究布依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物质生活文化方面,摩经中最有价值的是记录了有关居住条件演化发展的历史,对研究布依族甚至百越民族建筑史具有重要价值。
民族学资料表明,人类远古曾普遍有过一段穴居野处的历史。汉文献中所谓“太古之初,穴居野处”, [7] 和“古之氏,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居处下” [8] 等记载,说的正是这种居处情况。
从布依族摩经中的记述看,与汉文献关于“穴居”的记载不同,远古布依族先民经历了从树居到逐渐发明房屋的过程。《殡亡经·亨闷》中唱道,在学会建造房屋之前,人们:
这是一幅生动的树居生活图。而这种树居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巢居”。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就记载了南越人的这种居处习俗。看来这是越人早期较普遍的居住方式。摩经中只说是树居而不是穴居,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布依族先民生活的真实记录。所谓树居,就是在树上搭或绑上一些横木,在横木上铺上草栖息,就像窝巢一样。这种巢居方式后来演化成了“干栏”建筑。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这种建筑样式形成的原因是:“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这分析很有道理。布依族生活的地区除周去非所说的虎狼多外,还有林茂多蛇和潮湿等特点。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人们选择了树居这一较佳方式。当然,这并不排除布依族中可能也有穴居的情况。
干栏建筑是古越人(包括布依族)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注意到了干栏建筑普遍有晒台这一特点,从晒台的独特功能——晒粮这一因素把干栏建筑与稻作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干栏建筑似乎是稻作文化的派生物。 [9] 的确,干栏建筑的晒台与稻作的联系恐怕是存在的。但是,把整个干栏建筑说成是稻作的派生物就未免言过其实。要说“派生物”的话,也只有晒台还说得过去。人类的定居生活是随农业的发明和推广而逐步实行的。但并不意味着住房是定居生活出现的同时或之后才发明出来的。定居之前的“不定居”只是相对而言。实际的情形应该是:原始人每迁徙到新的一地,必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停留时间。因为新的地带天然食物可能只够食用一两天。从布依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食物来源有鱼类、野兽和野生植物以及果实等,比较广泛和丰富,因此农耕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定居并非不可能。在这种或长或短的居留期间,先民们由简而繁发明出住房,是非常自然的。从摩经中的叙述我们看到,人们过了一段游移的树居生活后:
终于,最初的房屋发明出来了。这可说是一种对历史的真实记录。“用芦苇作柱子”,“用苦竹作檩子”等绝非漫不经意之说,而是反映了工具还非常原始的条件下,对最适用于作房屋的建筑材料合乎常理的选择。而“汝”树叶,冬兰菜叶宽大,人们用来作房顶的遮盖物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看到,历史和逻辑在这里统一得多么和谐!而且,这段记述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古越人从树居到木质干栏建筑的中间过渡是竹料建筑。联系到汉文献中对百越民族集团中一些民族居所的记载以及今天作为古越人后裔之一的傣族中还存留着大量竹楼的情况看,这一假设并不是不可能成立的。
用竹作柱,以叶作顶的房屋当然是太简陋了,经不起日晒雨淋。摩经说,后来有—个叫“囊”[na:ŋ2]的人出外周游,学会了建造房屋的技术,回来后便架炉打制铁斧、砍刀,上山伐木,建成了木质结构的房屋。这表明,木质建筑是在金属工具普遍使用之后出现的。因而它反映的正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囊”在布依语中是对有尊贵社会地位的女性的称谓,因而由此还可看出,布依族房屋发明技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女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摩经中,关于伐木制作木器的记述不少。虽然其中打上了一些汉文化的烙印, [10] 但我认为这是对经文统一编订时掺进的成分。布依族祖先从树居到干栏建筑的过渡不可能是在接受汉文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布依族地区征集到不少铜制器具(其中有铜斧、铜锄等),经鉴定,为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遗存之物,其风格之独特,可证明是布依族先民铸造的。 [11] 这种金属工具的时代本身就能够说明木质建筑的历史。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七干多年前的干栏建筑遗存,证明百越民族木工技术历史悠久。摩经中有关木器制作的记述应该说是古越人这一文化特点的反映。
2.摩经反映的布依族制度文化
在布依族古代制度方面,摩经也为我们贮存了很多宝贵史料。这里着重谈谈社会政治制度和婚姻制度。
关于布依族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学术界曾经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布依族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因为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布依族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摩经中的一些内容可以支撑后一种观点。比如,在《安王与祖王》中,有关用人口作租向安王上缴的情节,就反映了布依族古代曾有过买卖奴隶的历史事实,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布依族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的反映。 [12] 这看来还是可以成立的。但《安王与祖王》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并非仅此而已。如果联系到整个摩经,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布依族历史上曾建立过国家。
我们先看“王”以及有关记述。摩经中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冥世有一个王[waŋ2],即最高统治者,而一般人的鬼魂进入冥界后就成了“王”室成员。在一些地区,摩经文学中对亡灵的称谓分别为“报光”[pau5kua:ŋ1]和“亚囊”[ja6na:ŋ2]。这两个称谓在布依族古代是对出身高贵的男性和女性的敬称。《射日·洪水》中也出现了“王”的形象。《安王与祖王》中除了“盘果王”、“安王”和“祖王”外,还有居住在天上的“王韶”[waŋ2θa:u2],等等。
王这一称谓在布依语中指国家最高领导者,或者首领,也可以指造物主。
[13]
但摩经中的“王”显然不是后两种意义上的“王”。因为冥界中的“王”似乎只有一个,而《射日·洪水》中的“王”拥有好田地可用来招募射日者,俨然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最高君主。《安王与祖王》中,“安王”之“安”[

根据唯物史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阶级分化出现的前提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白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的国家起源的几种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即是农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农业发展使社会出现贫富不均,私人利益冲突,而古代习惯法又不足以规定权利和义务,社会监督的新措施便成为必需,于是国家便产生了。这个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如前所述,布依族的农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很早就进入了犁耕阶段,因此布依族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也应该是比较早的。这无疑为布依族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关于布依族历史上是否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伍文义曾根据摩经《柔番沃番钱》撰文探讨过布依族古代的国家观。他虽然没有明确肯定汉文献上记载的古代国家中哪一个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但在他看来,布依族历史上曾建立过国家,这是无疑的,否则难以解释布依族古歌中为什么早已形成自己的一套国家观念。 [14] 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在布依族地区曾先后出现过牂牁、且兰、夜郎等国家,但由于汉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所以它们的族属至今仍是悬案。根据历史地理学、地名学等各方面的情况,夜郎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应该是没有疑议的。 [15] 如果从分析布依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入手,再结合其他文献史料、地下发掘和古歌等,摩经中的记述对探讨这些古代国家的族属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摩经中有关婚姻形态的记述也较丰富。《射日·洪水》中的兄妹结婚,是远古血缘婚中的“记忆”;《温经》中关于情人多易进仙界的观念以及举行情歌演唱仪式送亡灵登仙界等,反映的正是一种对偶婚制的遗迹。但摩经表明,布依族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已十分久远。例如,《安王与祖王》中虽然还有母权制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父权制已较为牢固。从整首古歌表现出的对安王的颂扬和对祖王的批判上看,当时长子继承权已经确立。这对澄清有关布依族婚姻习俗中的一些错误观念来说,又是一条有力的证据。
此外,摩经中对纺织和服饰、商品交换、民族关系等方面也有记载。兹不赘述。
3.摩经与布依族宗教、哲学和伦理
摩经中贮存了布依族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料。这里主要对有关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但大多从神话与史诗中进行总结,很少注意到民族传统宗教经典。布依族哲学以及道德观念方面的研究也不例外。其实这是不够的。
哲学是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总的看法。摩经分别由不同时代的作品构成,它反映的布依族哲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有的甚至相互抵牾,但这一点也许正是其重要价值所在:一方面,它反映了布依族精神文化的丰富性,同时,通过各个时代积淀下来的哲学思想材料进行条分缕析的清理,能探寻出布依族精神文化发展的轨迹。
摩经中体现出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唯心主义的因素比较突出。例如对人、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即是如此。从摩经中的变形观念一物由另一物变来这一特点看,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唯物因素。当然它是一种朴素的、机械的唯物论。
摩经中对事物来历的解释反映了一种发展和进化观点。在布依族先民看来,某种事物形成是其他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质变的结果。例如鸡是由鱼变来的。《嘱咐·引路鸡的来历》说,有两婆媳下河打鱼,回家后将鱼埋进沃土里,三五场(集、墟)过后,鱼变成了一种有翅的动物。燕子、“若汝”鸟飞来作它的“老公”、“丈夫”。后来就下了一大窝蛋,孵了二十五天,就孵出许多鸡来,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进化观,但它蕴含了朴素的进化观念。有的作品中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十分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如前述对住房发展史的勾勒就如此。又如《射日·洪水》中将洪水灾害发生的原因归结于“王”的食言。对“王”的不守信用的微词中,实际上又隐含了干旱是由于“王”无道而造成的观点。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摩经中记述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布依族处理社会成员之间、邻里之间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特定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
这些准则、规范有的是通过“训诫”的方式规定下来的。例如《嘱咐经》中亡灵对生者的嘱咐就是这样。有的通过死后住所的不同安排来表明人们对善恶两种行为的态度。在说明子女应对父母履行义务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忆恩》、《问窝问义》),或用讲故事的形式,使子女明白应该孝敬父母的道理(《迪云的传说》)。
勤劳、俭朴、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等等,是摩经中倡导的美德;而偷盗、抢劫和赌博则是人们厌恶的恶行。“你们要认真种地/种地才有吃的/神仙才保佑。”“三月做地里活/四月做田里活/妻约夫早起/夫约妻早起。”女婿和女儿吵架,不应该伤害娘家人。死了父母的孤儿寡女,邻居伯娘要关心、照护,哭时安慰他们,衣服破了代为缝补。赌博是一种恶习,千万不能染上,染上会败家(均见《嘱咐经》)。抢劫、偷盗的人死后进不了仙界,只能在去冥界的中途一个特定的地方受苦(见《登仙经》)。这些观念有的虽然含有迷信因素,但其内核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有的道德观念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具体分析。例如摩经中反对“惹官司”,理由是“惹官司”会“败家”(《嘱咐经》)。如果就不要“惹事生非”而言,当然是可取的。但如果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被侵犯,因怕“惹官司”而不据理力争,这就显得十分消极了。当然,作为旧时代产生的摩经文学,这种无原则的怕“惹官司”,实际上是布依族人民在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下有冤难伸、有理莫辩的悲惨境况的反映。
有的道德准则明显是对妇女的约束,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例如,女儿不能和儿子平分家产;出嫁到夫家后,家里有公公婆婆不能坐火炉上方;不能和公婆对面站;不能张口大笑;要坐在避人处等等。否则会被认为没有教养(《嘱咐经》)。这些在今天看来可说是十分消极的。
摩经还反映了亲子之间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准则。具体说来就是父母对子女有哺育和教养的义务,子女则对父母有赡养和送终的义务,即尽孝道。谁违反都将受到非议和谴责。在《忆恩》中,对父母如何千辛万苦抚育儿女的细致、不厌其烦的叙述,其目的既在于启发和强化子女的尽孝意识,同时也在于为作父母者提供一个如何行父母之道的榜样。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出于对人民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孝道,把孝说成是上天规定的道德律则。因此,孝是人们应遵循的最高德行,“人之行,莫大于孝”。从而不孝构成的罪行也最大,“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之所以把“孝”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16] 这样,调节亲子之间关系的“孝”,便被改造成了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了。
与这种人为拔高“孝”的适用范围的情况不同,摩经中的“孝”还保持着它的“原生形态”。而且,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与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同时并重的。
存在决定意识。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17] 哺育幼子可说是人类从动物那里带来的天性。在氏族社会里,为了使孩子长大后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氏族内部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如很多民族中的成人礼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尊敬年长者,在人类进入农耕阶段后就成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了。因为农耕生活比起主要靠强健体力的狩猎生活来,更需要的是经验。经验一般与年龄是成正比的。于是老年人受到尊重。进入阶级社会后,原来的氏族逐渐分化为若干个体家庭。家庭成了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氏族社会时期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性现在大幅度地具体化了。父母对子女的精心哺育和培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义变得愈发突出。家庭的职能越来越强化。历史在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前进。失去一方,另一方处境就变得艰难。
《殡亡经·问窝问义》中分别从子女和父母两个角度唱述了缺少对方时,自己命运如何悲惨,形象地揭示了这个道理。从父母角度看,没有子女者晚景凄凉。作品唱道,有子女者“回家晚了有人接”、“跌倒了有人扶”,相反则“自己跌跌撞撞/跌死也没人过问/自己跌跌撞撞/只能自个儿呻吟命苦”。有子女者,年老多病不能动弹时,有人垫垫枕头,端茶递水服侍。而无子女者,“饭碗放枕边/想吃饭也白搭/自己跌跌撞撞/呻吟死去也无人过问/自己跌跌撞撞/独自叹命苦”。从子女角度看,成了孤儿后失去了依靠和家庭的温暖,生活也无限悲苦。作品说,有父母者,外出时家里有人照看,吃饭时有人叫唤。无父母者情形恰好相反,因此孤儿只能“在寨子中间孤零零坐着/悲叹自己命苦/想到父就抹眼泪/想到母就泪如雨”。春节过了,有父母者进学堂,无父母者则上山打柴;有父母者打柴挑草回家就能吃上熟饭,衣服破了有人缝补,无父母者则只能吃残汤剩水,穿破衣烂衫,等等。 [18] 我们看到,当一方失去了另一方,他们的无助、悲凉表现得多么突出!这种悲哀感有的虽具有信仰的因素(如无子者担心死后无人上坟和祭供),但基本上是出自于生活上失去了照顾、依靠和温暖的现实原因。这种生活上亲子之间依赖性的增强,一方面是家庭职能强化的反映,同时也是布依族亲子之间道德准则产生的基础。
摩经中贮存的布依族精神文化材料当然不止这些。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看到摩经对我们研究布依族精神文化以及民族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摩经对布依族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指出:“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也像其他任何信息的传递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实现的: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品,通过手势等等。而这种传递的主要形式,是语言——口头信息(口头的或者书面文学的)。” [19] 摩经就是以语言形式传递着布依族文化信息的。摩经本身的形式特征,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作为一种信息源,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影响着布依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这种文化信息的传递首先是通过宗教仪式,以及作为仪式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文的演唱。自然,除布摩外,经文的内容一般人不可能全部知晓,也无必要或不想去知晓。但是,有的仪式项目是某种身份的人必须参与并且要求记住经文内容的。比如在吟诵《嘱咐经》时,孝子须全部跪于灵前听诵,因为其中有死者对亲人的嘱咐。在云南省罗平县以及贵州省兴义一带,丧葬仪式上的情歌对唱和《问都朵》 [20] 分别由死者女婿家和外家请人来演唱,因此这两类歌不仅布摩懂,一般人中懂得的也不少。从听众角度说,情歌对唱无论在何地,都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仪式。尤其是青年男女,这个仪式一开始,便围在演唱者(布摩或死者女婿请来的歌手)周围,悉心听着,情绪随着内容的变化而波动。因此,在这样一些仪式上吟诵的经文实际上为很多人所知晓,它对人们的影响就比较直接了。
问题主要在于,摩经之发生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其内容的知晓。由于对经文咒语般的语言力量根深蒂固的相信,加上诵经时伴随着的象征性的仪式动作所具有的神秘性,诵经这一行为本身就足够给人们以强烈影响。在这里,人们种种复杂的情感得到了宣泄,愿望似乎得到了满足,信念再一次得到支持,归属感内聚力得到加强……而这种影响是通过经文结合仪式进行吟诵造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得以实现的。
摩经中的文化信息更主要的是通过布摩这一中介和布摩举行仪式这一途径进行传递的。布摩掌握着全部经文。摩经的形式以及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容,对布摩来说,可说了如指掌。在某种意义上,把布摩称为布依族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点也不过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一般都有较高的地位。而且,历史的指针越是往后拨,这种地位越是显得突出。当他们根据经文对某种现象进行解释的时候,当他们按照经文中的规范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评判或者指导的时候,摩经对布依族社会的制约和影响便产生了。
摩经对布依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主要从伦理道德以及文学、戏剧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便获得较为具体的认识。
人的行为受心理、观念的支配。摩经中的道德观念支配、制约着布依族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态度。
与其他宗教形态一样,摩教也具有道德说教和道德约束的功能。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都是有原罪的,因此人必须行善才能得到救赎。佛教和道教则通过因果报应的观念,倡导人们行善。摩教的道德约束功能主要通过两个层面来实现。首先,通过对死后灵魂归宿的安排给人们一种压力,使人积极向善。按照摩教教义,人在世时行善,没有恶行,死后灵魂就能顺利通过连接阴界和阳界的“峤龙”、“峤法”(直译即“铜桥”、“铁桥”,相当于道教信仰中的奈何桥),而在世有恶行的人,灵魂上了“峤龙”、“峤法”后,桥面会越走越窄,最后窄如刀刃,无法通过,于是跌落于桥下成为孤魂野鬼,受尽苦难。其次,直接训诫,教导生者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处事等等基本道理。没有唯物论观念的人对自己死后的归宿都异常关心。可以想见,在世时有抢劫、偷盗等恶行意味着死后进不了极乐世界,只能在阴阳两界之间成为孤魂野鬼四处游荡,受尽苦难,这对人们所能产生的震慑作用有多大!它甚至能重塑一个人的基本人格。而摩经中“舅家五代走,外家五辈拜(年)” [21] 这句经典性的语言成了人们的一种信条,一代一代地实行着。直到今天,布依族中每年春节给曾祖母的外家拜年的情况仍不在少数。此外,布依族青年男女的“囊哨” [22] 习俗,从形式上看,无疑是对偶婚制的遗迹。但在一夫一妻制早已确立,并且婚姻封建化早已就很严重的布依族社会中,为何还允许它存在?过去我们都习惯于说布依族有恋爱的自由,婚姻却不能自主。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一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实际上,这跟摩经中“情人多好进仙界”这一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应该着重指出,“囊哨”活动中青年男女之间虽可自由与若干异性结交、对歌,即“囊哨”(从女子角度称“囊冒”),但也受着另一条规则的制约,即婚前或婚外性禁忌。这种禁忌也以宗教信仰的力量加以维护。 [23] 因此,“囊哨”实际上是一种“乐而不淫”的社交和娱乐活动。
摩经中的勤劳、俭朴、互相帮助、尊老爱幼以及戒赌、鄙视偷抢等道德观念,对布依族中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应该说,这些都是布依族社会中固有的美德。摩经作为一条永不干涸的信息源,经过不断的传递,使这些美德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扬。
与此同时,摩经中的消极因素对布依族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笼统地厌恶“吃官司”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人们卑怯、软弱、不敢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敢维护自己尊严的性格模式。当然,这种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而惨痛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但今天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应指出其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对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都极为不利。又如,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和教养,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都是需要的。但在摩经中,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这方面的道德观念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狭隘性。例如,过分看重血缘关系,在《鳏寡孤儿歌》中,摩经用一种十分抒情的格调来吟诵亲子之间失去对方后的凄凉。动人的吟诵,无疑强化了骨肉之情,增强了相互之间的责任感,从而造就了人们注重感情的性格特点以及无数的孝子和慈爱父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在这种浓重的亲情面前,“博爱”被排挤了,超出亲情范围的整个群体的事业也看不见了。而且,由于看重血缘亲情,无子女特别是无子者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比如,当仪式上吟诵到《鳏寡孤儿歌》和《问都朵》时,如果诵者本人没有儿子,就会联想到自己,从而哽咽唱不下去,听众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则会泣不成声。笔者在云南罗平县调查时当地人告诉说,吟诵这方面的经文时,无子者都不愿去听,以免触动心事。这实际上反映了在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抚育子女和养老只能依靠家庭的社会现实,当摩经反映的现实与真实的社会现实发生重叠时,必然触动人们心灵深处和情感深处最柔软的部位。此外,摩经中对妇女行为准则的“规定”,既是布依族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种反映,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这对布依族妇女的真正解放,对布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都极为不利。
总之,摩经中思想观念的复杂性给布依族社会生活以不同的影响,但忽视它同样是不可取的。
摩经是吸收各个时代民间文学作品,同时编创部分作品逐渐形成的,在传承过程中,又反过来对布依族民间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直接的莫过于借用摩经的作品,加以创作,在适当的场合吟唱。如《温经》中的鳏寡孤独歌和情歌等作品就是这样。其中以情歌最为突出。情歌对唱的形式之所以吸引青年男女,绝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和娱乐,还在于他们都想在这样的场合学会一些歌。摩经中的这些作品也许是从民间文学中吸收进来的,就像存入了仓库,可以随时取用一样。在很多布依族地方,汉语山歌已成为主要的民歌形式,青年人会唱布依语情歌的已经很少了,如果想学一些母语民歌,就跟布摩讨教或到丧葬仪式上去听。由于这些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加上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演唱能使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作品的内蕴和情感,因此它最能打动人的心灵。
摩经对布依族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布摩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这种影响可说从很早就开始了。它与布摩的特殊身份有关。可以说,甚至布依族韵文的一些特点(比如复沓)都是布摩的创造。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时间推到远古时代。毫无疑问,远古时代布摩的主要任务是行使巫术。如果万物有灵论可以成立,那么灵魂观念产生之前布摩就已出现。在巫术中,语言的力量被格外看重。尤其灵魂观念产生后,对付灵魂这一特殊对象更是这样。
这种“语言”从形式上说当然不同于一般用语。从摩经看,它全部由韵文组成。其中肯定有比较原始的作品。人类学资料表明,在原始人那里,有节奏的韵语具有一种魔力。“刚果地方的土人说:歌谣是用以和别个世界的人交通的,是用以对‘上面的人’即天上的人讲话的”,某些歌谣“有咒文的性质”,或“有厌胜之意”。 [24] 金克木发现:“在古老的印度人心目中,诗歌不但可以治病,而且可以驱邪降妖,当然也可以害人。为了防备别人诅咒,就要有反诅咒的咒语。这是用语言作武器进行幻想的斗争。” [25]
布摩在行使巫术时不采用怪异的动作,这说明布摩并不把怪异动作所能达到的效果看得怎么了不起。因而,巫术中语言的力量就更显示出其重要性了。为了加强巫术的效力,布摩把相同意思、相同结构的句子或段落加以重复吟诵。于是我们在布依族韵文中看到的鲜明特点——复沓、对仗和排比就形成了。
关于诗歌的复沓,学者们曾进行过各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便于记忆;有人认为是远古诗、歌、舞三位一体,诗歌配合舞蹈节奏而形成;也有人从少数民族对歌风俗入手,认为是对歌这种演唱形式造成的。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令人感到不够完满。如果考虑到巫术在人类文化史上出现的时序较早,考虑到语言——有韵有节奏的语言——在巫术中的特殊意义,那么,这样的解释我认为是较为合理的。至少,布依族韵文中的复沓、对仗与排比只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解释才比较令人满意。
人类学资料还表明,原始巫师同时也是歌手。布依族中也不例外。现在还可看到,布摩大多是歌手。由于这样一种身兼“二职”的特点,布摩根据巫师的手法和特点创作出一般的韵文作品,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范本和文体模式。灵魂观念产生后,布摩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对鬼魂进行处置的模仿巫术,由于内容本身表现一种过程,具有情节性,因而,它无疑为布依族叙事性韵文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摩根据民间神话、传说创作出新的作品,使摩经的类型不断丰富,内容不断充实。之后,既是祭司又是歌手的各代布摩又充当一种媒介,把摩经的信息(包括形式和内容)通过不同途径传递到人们中间,对布依族民间文学创作不断发生着影响。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摩经和民间文学都有佚名性的特点,因此从具体作品来谈它们之间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似乎比较困难,能做到的只是就两者的相似点作些推测。比如,在望谟、册亨、贞丰等地广泛流传的叙事长诗《金竹情》,以及安龙一带流传的传统布依戏《胡喜与南洋》,可说是地道的民间文学作品,可是流传于荔波一带布依族中的以求子保子为目的的傩仪经文中,就有在故事情节、人物等方面基本相同的一卷《范龙》。这些作品中叙述男主人公家如何请人到女主人公家求亲,女方家如何请布摩推测出嫁日子,以及推测的吉日为“彪”日(即丑日)等情结,又与贞丰县一带摩经《女儿祭》中的一段惊人的相似。我猜想,这些作品中的有关段落受摩经《女儿祭》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宗教仪式对布依族戏剧也产生过一定影响。过去,布依戏有的剧目的表演场面大,时间也拖得较长,一出戏要演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显得很不集中、凝炼和紧凑。这与宗教仪式的表演很相似。自然不能说布依族戏剧表演形式是从宗教仪式演变而来,但前者受后者的启发或影响的情形肯定是存在的。宗教仪式实质上是一种模仿巫术形式。而由巫术形式分化出艺术形式,艺术史上不乏其例。卢卡契指出:“虽然巫术模仿形象不论内容还是形式的确定都是与审美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在客观上由此却奠定了形成对现实审美反映的基础。” [26] 这很有道理。现在布依戏的形成问题正在讨论之中,如果考虑到摩经的演唱形式和特点,也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总之,摩经作为一个信息源,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着布依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要深刻认识布依族的固有文化,就必须对摩经有所了解。
(四)摩经的传承
摩经的传承有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主要靠布摩。从世界几大宗教的情况看,一般信众都要诵读经文,把诵读经文作为与神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和手段。摩教虽有类似情况,但范围很小。例如在一些生活巫术中,普通信众也可以通过默念咒语直接作用于施术对象,企图用语言的神奇魔力使对象就范或伏法,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但总的看,摩经的学习和使用仅限于布摩。因为人们认为,摩经是说给鬼神听的,所以一般人不得随便诵读摩经,只能由具有专门技能而且受到祖师爷报陆陀保护的布摩诵读。由此看来,摩经的传承具有更为明显的职业性质。这使摩经的传承链条十分脆弱,往往是随着布摩的去世,摩经传承即发生断裂。
其次,由于摩经传承的职业性,摩经采用拜师学艺方式进行传承。通常,一个人想成为布摩,就拜某个交摩([ʨau3mo1],布摩师傅)为师傅,向其学习摩经,一边学习,一边参与有关仪式,当学习者掌握了摩经,并基本掌握了所有的仪式程序之后,应学习者的请求,交摩举行“出师”仪式,将举行宗教仪式的秘诀和资格授予学习者,使之取得独立举行宗教仪式的资格。取得这种资格后,意味着该布摩具备了“独立门户”的资格。一方面,该布摩可以独立举行一些小型的宗教仪式,同时,自己也成为布摩师傅,可以带徒弟,率领和指挥徒弟举行大型宗教仪式。当同时有几个大型的宗教仪式需分头进行,就能分出人手,满足这种需要。
因为大型宗教仪式活动都需要几个布摩共同配合协作才能完成,所以布摩通常都有一个由师徒构成的班子。并不是每个弟子都能取得“出师”的资格。在布摩的若干弟子中,总有各个方面表现不一的情况,师傅就从中选择那些聪颖、禀赋好、忠诚、正派的徒弟重点培养,有意识地逐步放手让其担当一些重要仪式活动的主持,待时机成熟,并应该徒弟的要求,择日举行“出师”仪式。和其他职业一样,师傅在传授过程中总留有一手,即一些关键的技术或秘诀不传授,经过考验证明弟子确实忠诚和值得信赖,才向其传授。布摩在传授摩经和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技术”时,也是这样,一些秘诀也只能到了举行“出师”仪式时才能授予。
三是摩经一般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虽然绝大多数布摩早已采用汉字记音的方式,并借用汉字偏旁部首用汉字六书造字法创制了一些文字符号来记录布依语特有的读音,摩经因此早已成为一种成文经典,但在传授摩经时,布摩通常仍采用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当某人有了想当布摩的意愿时,或布摩认为某人适合从事这一职业,对其进行动员,这人也愿意后,学习者和传授者就约定时间,学习者到布摩师傅家里学习。布摩从事宗教仪式活动都是业余的,平时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学习摩经一般选择在晚上。传授时,师傅不用经书,一句一句教给学习者,学习者也在没有任何书本的情况下,一句一句地学习、默记。直到能背诵为止。当学习到能背诵基本的经典后,就逐步参加宗教仪式活动,亲身实践,掌握宗教仪式程序和礼仪。
摩经既然早已成为一种成文经典,为什么还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语和布依语虽同属汉藏语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各自的语音系统和语法规则,因而用汉字记下的音和布依语音完全相同的非常少,大多数的情况只能是相近。此外,经常有一个汉字记录几个布依语音的情况。例如,用汉字“拜”(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发音为[pai35])就可以记录布依语词[pai1](意思是“去”和语助词“了”)、[pat7](意思是“佛”),[pai1](“去”、“了”)与汉语发音还算接近,但[pat7]在汉语中,起码是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中,绝对找不到相同或相近的发音,因为其语音系统中已没有了[p][t][k]这样的韵尾;汉字“然”(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发音为[ran21])可以用来记录布依语词[ða:n2](意思是“家”)和[ðan1](意思是“见”),有的还用来记录[ða:ŋ2](意思是“笋子”),其中布依语和汉语语音相近的只有[ða:n2],另两个音相差就比较大。因此,汉字以及新创文字符号记录的经典,只能起到提示和帮助记忆的作用,如果完全依赖经典,按汉字读音读出来的绝对不可能复原摩经本身,只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次,记录摩经的汉字相当多,这就要求学习经文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汉文水平,否则,不要说汉字不能准确记录布依语音,即使是那些能准确记录布依语音的汉字,如果连汉字都不认识,是不可能读出来的。布依族地区虽然清代就有了汉文学校教育,但20世纪50年代以前,布依族地区汉文学校教育仍然非常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懂汉语识汉文者不断增多,但总的来说文化教育还是显得比较落后,能完全读出经文中的汉字者还是比较少的,这样,摩经的传承当然只有延续传统的方式了。
布摩发展徒弟有优先在家族内选择的特点,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家族传承特征。这是因为布摩在社会中有较高社会地位,布摩当然希望最大限度地使本家族保持这样的社会地位,所以在接收弟子时,总是优先考虑本家族子弟,这样,就形成了很多布摩班子家族化的情况。例如,根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调查资料,贞丰县北盘江镇坡色布摩班子就全为罗姓家族成员,冲冲寨布摩班子则全为梁姓家族成员,尖坡乡布摩班子基本上是韦姓家族成员。但是,由于成为布摩需要一定的禀赋和素质,如果一味考虑家族内发展的原则,就可能造成布摩后继乏人的现象,例如,在多姓氏杂居村寨中,如果各姓氏中没有哪一个姓氏在人数上占多数而是比较均衡,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本家族内找不到适合做布摩人选的情况。因此,家族化虽然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但并非绝对化的要求。
(五)摩经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出版
尽管由于左的思想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摩经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时刻意隐瞒其经文性质,把它作为民间文学来处理,但客观上搜集保存了摩经中一些重要作品。因此,它也是摩文化调查研究中的成绩之一。由是观之,摩经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可以说是摩文化调查研究中成绩最突出的方面。
摩经借用汉字记录,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50年代初,王伟教授率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民语系学习布依语的一批学生到贵州省罗甸县罗捆一带进行教学实习,调查并记录了当地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用汉字记录的经书(布依语称sɯ1mo1,即“摩经”),可谓开布依族摩经发掘之先河。同一时期,布依族老一辈的民族文化工作者黄义仁先生等也深入到罗甸等布依族地区发掘、搜集了大量的布依族摩经。紧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语言普查中,又有不少布依族摩经抄本被发现。但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出版印刷条件,所发现的摩经材料没有能以其本来的面貌公诸于世,一部分经过翻译、改编之后,以布依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形式整理出来,作为内部资料载于相关集子。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州文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联合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45集《布依族古歌叙事歌情歌》,其中一部分古歌实际上就是根据布依族摩经的内容进一步整理的。汛河等整理的《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兴年月时辰》、《造千种万物》等等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搜集的。因此,50年代的重大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发现,即对布依族摩经民间抄本的发现。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以摩经为代表的布依族文献古籍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文革”期间大多数宗教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布依族民间摩经抄本也被视为“四旧”的产物而遭收缴、焚毁,多数地区的摩经都在这一时期被附之一炬。学术界对摩经的发掘、整理也基本停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以后,作为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布依族摩经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工作才逐渐得以恢复。
为了配合布依族新文字方案的试行推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贵州省布依族聚居的各县(市)有关机构便着手开展对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抢救,翻译整理出一批摩经。如韦廉舟、吴启禄、赵焜对贵阳市花溪区把火寨、董家堰、龙井寨、四方河、新民村以及乌当区的新堡、偏坡、罗吏等村的布依族牛经书(即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将整理翻译出来的把火寨牛经书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65集,供研究参考。该资料集采用80年代初修订的布依文方案记录当地牛经书的读音,每个布依语词下面有汉语直译,最后是汉语意译,没有附原文,这对于文献古籍的保存和研究来说是一种遗憾。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黄义仁、黎汝标等学者对流传于黔南以及黔西南部分地区的布依族摩经和其他一些文献古籍进行了搜集,经整理翻译后的古籍作品约70多万字收入1998年出版的《布依族古歌》中。该书所收的古籍一部分采用汉字注音原文、新创布依文、国际音标和汉文直译四对照的形式,为学术界研究布依族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柏果成、黎汝标还对荔波布依族生育傩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发表于《中国傩戏调查报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伍文义也在布依族摩经古籍调查和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王开吉、王国佩合作翻译整理的贵州省兴仁县明光村《接龙经》和《敬官厅经》载于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编印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六集(布依族)。90年代他还对威宁县新发乡花园村的摩经进行了调查。
除《布依族古歌》以外,90年代还先后正式出版了《安王与祖王》和《古谢经》,可以说是布依族摩经翻译整理成果丰硕的10年。
《安王和祖王》是布依族摩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摩经中都有这一节,只是内容详略不一,名称也不完全相同。1994年出版的望谟版《安王与祖王》在民间没有手抄本,由望谟县民委黄荣昌、黄仕才二位同志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记录整理,并作初步翻译,90年代初经中央民族大学王伟教授校订布依文和国际音标,周国炎对译文进行加工、润色,并对全文进行统编,最后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望谟版的《安王与祖王》是目前发现的布依族篇幅最长的叙事史诗,全诗1700余行,用优美的语言生动地记述了布依族原始社会末期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状况,是一部反映布依族古代社会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研究布依族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布依族摩经的艺术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它的问世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望谟县纳魁村的《祖王与安王》共1600多行,由韦永奎搜集整理并翻译,发表于1997年出版的《布依族摩经文学》,但该书只刊载了译文,没有原文。望谟搜集到的《安王和祖王》的另一个版本约有560余行,由黄义仁先生翻译整理,收入《布依族古歌》。册亨版的《安王》篇幅较长,共1500多行,由王汉文记录,卢衍翻译整理,载于1988年编印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六集(布依族)。此外,贞丰岜浩版和纳禅版的《安王和祖王》也都有手抄本,但篇幅都远不及正式出版的望谟白头坡版《安王和祖王》,其中纳禅版700余行,无标题,岜浩版(该套摩经中称《告王》)仅300余行,均已收集整理,但未正式出版。
《古谢经》是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最能全面反映布依族摩经面貌的布依族文献古籍,该书由贵州省安顺市民委和镇宁县民委合编,王芳礼、韦照熙、杨开佐翻译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古谢经》是布摩在超度亡灵仪式上吟诵的经文。“古谢”是布依语译音,直译为汉语是“做客”的意思。按布依族风俗,老人去世时要举行隆重的超度仪式。亲戚朋友都前来吊唁,这一风俗被称为“做客”,直译成布依语即“古谢”,因为摩经是在丧葬超度仪式上念诵的,所以称为“古谢经”。“古谢经”全书共分八卷,采用原文(汉字注音)、国际音标和汉文直译三行对照,并附意译,这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极为方便。翻译整理者精通布依语,汉语水平也比较高。译文既基本忠实于原文,又尽量做到语句优美顺畅。但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疏漏。如第5页左栏第一行原文的注音汉字为“丹”,国际音标注音却是ma35,汉语直译、意译均为“骂”。布依语本族词有“骂”这个词,普通的“骂”为


1997年由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摩经文学》收录了《开天辟地》、《造万物》、《造物与造神》、《十二层天十二层海》、《祖王与安王》、《射日·洪水》、《驱虫记》、《转场》、《开年歌》等15篇译自各地摩经中的宗教典籍文献的译文,该书仅有汉文译文,未附原文和逐字对译,而且一些篇目在翻译整理时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原文已不能完全对应,只能了解经文主要内容。
黄镇邦和霍冠伦(Stephen Hoff)搜集于望谟县蔗香乡林楼村并整理翻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布依摩经——母祝文》是超度母亲亡灵转世的一部经文,民间有手抄本,译注者采用原文(方块布依字)、布依文、汉语、英语四行对照的形式出版,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黄镇邦译注,2011年9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嘱咐经》采用原经文、国际音标、布依文、汉文直译、意译对照的方形,并做了较详细注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这个传说几乎在布依族地区均有流传,广西壮族地区也有流传。但各地说法不尽相同。就布依族地区而言,“颍”在一些地区是改革食人习俗的首倡和实践者,在另一部分地区则成了食人者。在后一类传说中,“颍”被说成是食人肉的野人。为了不让“颍”吃死者肉,于是用牛肉代替,相沿成习,一直到今天。
[2] 布依族简史编写组:《布依族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版;喻翠容:《布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3] 《布依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布依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4] C·A·托卡列夫E·M·梅列金斯:《神话和神话学》,魏庆征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6] 关于含“那”地名的分布、“那”与水稻耕作的关系等,游汝杰在《从语言地理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7] 《古史考》。
[8] 《墨子·辞过》。
[9] 鸟越宪三郎:《倭族之源——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10] 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所居皆竹楼,人处楼上,畜产居下,苫盖皆茅茨。”清·沈西霖《粤西琐记》:“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墙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
[11] 《布依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布依族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 《布依族文学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布依族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子和:《试论〈安王与祖王〉》,《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
[13] 第一种意义使用较广泛,皇帝、总统或主席皆称pu4waŋ2或pau5waŋ2。第二种意义现多含贬义,最初可能承袭对氏族部落酋长的称谓而来。第三种意义使用不普遍,有万物为“王”造的说法,比如山就是,甚至人对着山喊叫时发出的回声也被认为是“王”的声音。
[14] 伍文义:《试论布依族〈赎买经·柔番沃番钱〉的初期国家观》,《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15] 周国茂:《夜郎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夜郎研究——99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16] 《孝经》。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34页。
[18] 见贞丰经文《问窝问义》。另外,云南罗平经文《问都朵》[wan1tmk7to4]有类似内容:有儿有女者,热水放枕边,不想吃也劝吃;无儿无女者,水罐放枕边,想喝水却碰倒。有儿有女者,三月去上坟;无儿无女者,三月别人去上坟,他(她)无人去上坟……
[19] 勃罗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中译本第58页。
[20] 内容反映鳏寡孤独者的悲苦。
[21] 《嘱咐经》中亡灵对生者的嘱咐之词。
[22] 青年男女之间一种社交或谈情说爱活动。
[23]
私生子被认为是一种鬼,需处死。生下私生子的妇女身上也因而附上了一种叫“独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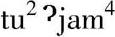
[24] 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25]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26] 卢卡契:《艺术特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中译本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