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彝文与彝族布摩
彝文文献《迎请布摩书》、《借布摩神力》 [1] 等载:“哎哺出现,采舍产生后,恳索出现,目确产生后,则咪形成,武侯出现后,布摩有源头。哎哺有布摩。”“尼能先形成,尼能先产生,布摩先产生,布摩先能言。”在说到布摩的传承时称:“先有尼能布,尼阿依布摩。阿依武布摩,十代尼能布,首推直米赫,首推乌度额;后有什勺布摩,十代作布摩,首推什奢哲,首推勺洪额,鄂莫布十代,首推鄂叟舍,首推莫武费;慕靡布摩二十代,首推恒始楚,首推投乍姆,妥梯布二代,首推吐姆伟,首推舍娄斗。举偶布摩在恒耿,署索布摩在恒默,六祖布摩二十代,在邛佐之后,六祖无布摩,邛佐就有了。武有六奢厄,乍有四开德,糯有三蒙蒙,侯有三尼礼,毕有三莫莫,默有四赫赫,六祖布摩二十代,是这样说的。”
《彝族源流》(卷十二) [2] 说:“哎哺先为布摩,哎阿祝布摩,奢哲吐布摩。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哺卧厄为布摩,厄洪遏为布摩,洪遏梯为布摩,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后为布僰氏,布奢哲为布摩,僰洪遏为布摩。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摩就有文,有布摩就有史,优阿武写文,啻赫哲编史。吐姆伟掌文,舍娄斗掌史,布摩创文史。”《彝族源流》(卷十二)还记录了布摩的传城谱系:局舒艾——舒艾氐——氐叩吐——叩吐额——额够葛——支恳那——恳那觉——觉直舍——直舍索——索勒易——布僰阿苦——苦阿额——额额努谷——苦阿度——度俄索(什勺氏的首席布摩)——俄索阿那(在妥米纪抽为米靡布摩)——阿那乍(在恒耿洪所为举偶布摩)——乍阿伍(在卓雅纪堵为六祖布摩)——阿伍恒租(在赫则甸体为亥直布摩)——乍阿莫——莫洛略(得三十章《额咪》和百二十《苏古》的真传)——布僰俄——僰俄乌——乌阿那三代(“乌阿那那时,子不继父业”,可向家族之外的人家传授布摩经籍)——始楚勾——勾迫稳——迫稳布那(遂行多种仪式的分工)。根据彝文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布摩谱》等记载,布摩出现在母系社会中晚期的哎哺时期,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哎哺后期,已基本定型,且形成了兹、摩、布(君、臣、布摩)三位一体政权架构的原型,即在这一政权架构里,以策举祖为君,诺娄则为臣,举奢哲为布摩,布摩即是这种政权架构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并作为一种模式,沿袭了数千年,为区别区分君、臣、师这三种职能,还各取一物作象征性标志:“鹤为君、杜鹃为臣、雄鹰为布摩” [3] 。从布摩的传承上看,尼能时期,有十大布摩,以直米亥和乌度额两人为代表,从事偶像的塑造与崇拜活动;什勺时期,有十大或八大布摩之说,以什奢哲和勺洪额两人为代表,在点吐山里(今云南大理苍山一带)兴起丧祭制度,这种习俗一直传到现代;米靡时期有二十大布摩,以布始楚、僰乍姆两人为代表,米靡时期是布摩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形成了十大布摩流派,到武洛撮一代,祭祖制度由恒阿德制订,以典章的形式传了下来;举偶有十大布摩,以额武吐、索哲舍为代表,举偶时期是布摩文献取的辉煌成就的时期,三十部《额咪》、一百二部《索古》都写成于这一时期。在“六祖”分支之前,邛佐氏继承了举偶布摩,“六祖”分支后,有二十大布摩:武家有六家奢厄,乍家有四家开德,糯家有三家蒙蒙,侯家有三家尼礼,毕家有三家莫莫,默家有四家赫赫。六祖分支后,在今滇、川、黔彝区,林立着数以百计的彝族世袭君长统治的各部政权,各部又都指定一家或数家首席或世袭布摩,《迎布摩经》载:“……主人商议请布摩,纪古地方布摩多,……东边布摩多,有举雨、有诺怒、有阿瓯威名,亥索如虎啸,却都在得远,远了请不来。西边布摩多,(阿芋)陡家有德歹布摩,笃(磨弥)家有直娄布摩,乌蒙家有阿娄布摩,有阿娄阿阁布摩,芒布家有依妥布摩,有依妥洛安布摩,……北边布摩多,阿租迫维是布摩,麻靡史恒是布摩,维遮阿尼是布摩,阿蒙举雨是布摩” [4] 。“……阿哲以亥索氏为布摩,举雨的布摩神是雾形,阿载的布摩神是鹰形,阿尼的布摩神是鸡形。……陡家德歹氏,芒布有益吉氏,益吉洛安氏,阿底家有支吉氏。……乌蒙部有阿收氏,阿收阿阁氏。益支布摩声望大,麻育布摩很突出,……还有毕余孟德氏,麻弥史恒氏,赫海(芒布)地方布摩济济。笃磨(弥)以德勒为布摩,又有阿租迫维氏,都是世袭布摩” [5] 。布摩的世袭是以土地的继承作支撑的,各部政权君长直到演化为土司的漫长时期,都给布摩世家一片可观的土地。为了土地的永久继承使用,就必须把职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也就造成职业的排他性和技能的保守性,为君长或土司服务的布摩成为土目,布摩的土地俸禄往往可以和土目的土地俸禄等同。“改土归流”后,土司制残存下来的土目家所择的布摩世家也一样给一大片土地作报酬,以至于布摩世家后来有了地主的成份。
在今贵州省及毗邻地区,水西部以妥目亥索、渣喇家为首席布摩,有毕余莫德等若干家世袭布摩,妥目亥索是水西阿哲的家族,共祖于俄索毕额一代。《大定府志》所录的“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称:“其先,蛮夷君长突穆为大巫,渣喇为次巫,慕德为小巫。” [6] 突穆即妥目亥索家;乌撒部以维遮阿尼、麻博阿维家为首席布摩,有德歹、举雨、阿都乃素等若干家世袭布摩;磨弥部以德勒、芒部以益吉洛安、乌蒙部以阿寿等若干家世袭布摩。这种传承形式主要延续到清康熙初年,少部分还延续到1949年前。
二、布摩职能的演变
1.布摩职业在传承中分化出了“摩史”一职。彝族布摩的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主持祭祀仪式、传承传播彝族典籍文化。布摩的这种职能沿袭的历史有着数千年之久。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分工的明细化,在布摩这一职业中,又分化出称之“摩史”的职业。
“摩史”有“摩守”、“慕师”等多种音译。摩史是古代彝族社会中的一种职业(职务),地位次于君长,是“穆魁”组成成员,又与在彝族政权结构中居于第三位的布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在水西彝族君长制政权体制高度完善的九扯(九个平行的部门)九纵(九位行政长官负责)设置中,摩史为官一秩,“司宣诵”,“司文书”,“掌历代之阀阅,宣歌诵之乐章” [7] ,集史官,礼仪官,外交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摩史必须做到通文字,精礼仪,足智谋,善辩论。举凡大典,外交应酬,祭祀祖宗,婚丧大事,都少不了摩史这一重要角色,“辄饮酒赋诗,竞才品艺。所赋诗歌,多古典古语,尤以能设比喻及隐语者为上,颇似诗经中以草木鸟兽咏成比兴体诗歌。” [8]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谕物”的记录,指的角色应当是摩史。
摩史在历史上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在各君长国时期,这一职业通常是由相当于亲王的人充任的,如阿芋路仁邓阿余、举足阿姆、芒布部阿额麻耐、水西部的支能额觉、举娄额尼、德楚仁育、乌蒙部的举足尼迫、乌撒部的陀尼德直、侯汝米勺等等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在兵戎相见的战场上,他们是冲锋陷阵的武士;在家族统治的政权里,他们是地位仅次于君长的摩魁;而在激辩的场合,他们又是能言善辩,口才出众的摩史。
摩史的礼仪官,外交官等身份使他们有展示才华的空间与平台,古代彝族各君长国之间的交往活动,即外交活动称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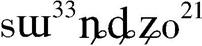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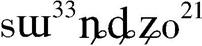
尽管随着彝族君长制政权的消失,摩史这一职业不复存在,但摩史曾记录掌握使用的那部分典籍仍然流传了下来。所谓布摩,应当是布(摩)与摩(史)的合称,摩史原先与布摩是一家,随着社会分工的具体化而从布摩中分支出来,失去职业存在的依托后又归入布摩,到后来,至少是由布摩传下原先属摩史掌握的那部分典籍,这正是摩史文献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实,布摩与摩史是有着渊源关系的,其一,布摩与摩史都以额索氏为共同的鼻祖,共同崇拜知识和智慧之神。其二,在丧祭活动中,共同主持各类仪式。布摩,摩史分别担当主客两个角色,在仪式中念诵经文典籍,在近现代的丧祭活动中,有布摩在大堂主持仪式,摩史在客堂主持仪式。亲戚家请来参与奔丧的布摩,充其量只是摩史的角色。他们只念诵本书即《摩史苏》一类的典籍,但却表明布摩与摩史之间,不论仪式上还是他们的典籍上都存在着相互交叉的情况。
2.布摩职能的根本演变。彝族布摩主要职能的根本演变主要是参政议政职能的丧失。在彝族政权时代直到土司制时期,布摩在很多时候是主持丧事祭祀和祖宗的祭祀仪式,又司教化,以家庭教育与布吐(学堂)教育的形式,教授本家族乃至于外家族子弟,传播彝文典籍文献文化。战时的布摩为君长决策出谋划策,制定军事谋略,有国防或军事参谋长一样的职能,如吴三桂进攻水西时,《布默战史》载:“在这天夜里,大毕摩谋臣,姆兹骂色,所有来商议,濯色兹摩(安坤),问毕摩谋臣:此番的舒啥,所率兵马,如雾霭进攻,似暴雨猛降,咱慕俄勾家,供祖桶神山,祖灵栖身处,已被占领了,君长的买待,必须规避。大毕摩谋臣,都认为恰当。” [9] 。水西乌撒两部械斗时,“德楚仁育氏,以地位显赫,尊贵为君长,……他下令兵马,收拾兵器,退出战斗。乌撒毕摩谋臣,还守着阵地,乌撒的战将,随那叔余优,好比猪见草,进那周阿吉,住的大帐内” [10] 。布摩甚至于还跟随君长,亲自领兵出征上战场:“布足布毕,跨善攀花马,布足果车,跨淌鼻涕马。这两位毕摩,玩镶银维庹,腰吊金葫芦,头戴镶金冠,牢洪显威仪,身着绸和锦,如林中连理,持两件利器,展英雄气度,有长者风范。……布铺阿诺,跨长尾虎马,布篝布祃,骑花斑虎马,第三位毕摩,骑始楚虎斑黑马,间隔两丈骑,弄镶银维庹,腰佩金葫芦,犹三重星临空,没有尽头般;犹半天云中,两雄鹰齐鸣,在树梢之上,众鸟不犯愁;似深山林野,两只虎齐啸,为众兽壮胆,犹牧羊遇兽,顺手就获取;犹如大老虎,来到点苍山” [11] 。
到了清代,随着承袭君长政权的彝族土司政权的结束,彝族布摩从前台走到后台,在朝走向了在野,专为少数土目地主的丧事祭祀和祖宗祭祀服务,同时更多为彝族民间的丧祭、祖灵祭奠、祭山、祭土地、祭水等各种祭祀仪式服务,还为民众举行祈福消灾、治病、择期找日、预测命运、占卜等活动,并积极招收一部分外姓弟子,传授彝族传统典籍及其布摩的职业,从而使演变了的布摩职能还可能传承到近现代。
三、文字文化的传承
彝文文献《彝族源流》卷十二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摩就有文,有布摩就有史,优阿武写文,啻赫哲编史。吐姆伟掌文,舍娄斗掌史,布摩创文史。”《物始纪略》也说:“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彝族源流》等载,彝族的君、臣、布摩出现在哎哺时期,这一时期,据《阿买尼(磨弥)谱》载:“在笃慕之前,有三百八十六代。”说明彝文文字及其古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彝文文字同样经历从符号到成熟文字的发展过程,彝文与刻画符号(陶文)能挂上钩,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有多人多次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乡出土一批陶文后,一批彝学专家也用彝文作了释读;同样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多个地方出土的刻画符号用彝文去释读都不是很难的事。彝文与刻划符号(陶文)应存在着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从载体上说,有以金文、竹、木刻、竹木简、皮书、构皮纸、石刻等为载体的发展历程。金文目前为止发现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系1972年在贵州省赫章县珠市乡铁矿村磨石沟出土,该擂钵经贵州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擂钵原件由毕节地区博物馆转大方奢香博物馆收藏,但目前不见展出。再是“蛙钮彝文铜印”,该铜印是1987年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现的,印体长4厘米,宽3.5厘米,印面厚2.5毫米,印钮与印面高1.5厘米,重39克。印钮为立体青蛙,呈蹲伏状,栩栩如生。印面系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符号,自上而下排列,刻工反刻,印面和字里行间有界格。铜印译成汉文应为“妥鲁(堂郎)山里手辖印”,可译作“统管堂琅印”。有人认为该铜印为西汉时期的文物。“统管堂琅印”现由云南省昭通市卫生局干部熊玉昆收藏。还有“夜郎赐印”,该印发现于贵州省威宁县境。铜印鼻钮,正面彝文,自上而下,后背及钮之两侧均作波纹状;钮在正中,作提形。该印由昭通的张希鲁先生交给原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子琴教授,后在“文革”中丢失,现云南昭通市博物馆木质复制件存放。西南师范大学邓子琴先生1979年4月发表的《彝文“以诺”印章跋语》中有介绍,此印由西南师范大学历史陈列室收藏,“文革”中遗失,现仅存拓片。在文献载体种类中,金属器物文献是无价之宝。
以竹、木刻、竹木简为载体,见于文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文献“木刻竹简,堆积如柴薪”或“堆放如柴禾”的记载。彝文竹简的残存,发现于四川凉山州的雷波县一带,现有原物存放于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和楚雄州博物馆内。木刻则有5部流传于云南、四川、贵州彝区内,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摩史苏》即其中之一。皮书即以牛羊皮为载体的彝文文献,在毕节地区境内残存有10件左右,其中较完整的是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牛皮文《余吉米体访亲记》1件。明清以来的数以万计的彝文文献都是以构皮纸作载体的。石刻为载体的文献有数千件,绝大部分也形成于明清时期。
从所传承的内容来说,布摩和摩史文献涉及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军事等诸多文化遗产承载,内容与文字传承互为前提又彼此相互依存,正是它的这种属性决定着其文字文化的传承的生命力。汉唐以来,彝族文字文化的传承始见于汉文献中,汉文献中较早记录彝文的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宋代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志蛮》胡启望、覃光广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版)也提及彝族罗殿国文字的事:“押马者,称西南谢藩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进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化的大环境中,在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强势冲击下,传承了千万年的彝族文字文化生存与传承等都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四、现实布摩的状况
布摩的传承已面临着严重的断层和断代的窘境。以原乌撒部故地的各世袭布摩家族为例,维遮阿尼(有王、叶、聂等分支)家虽然形成了较庞大的家族,但已无一人承袭这种职业,德歹(禄)、举雨(有余、安、禹分支)、德勒(有金姓和姬姓)、阿者(禄)等布摩世家的情况与维遮阿尼家族是一样的。麻博阿维家族(有文、黄、安、杨、张等数十姓)大量分布在威宁、水城、赫章、纳雍、大方等县,仅有赫章妈姑镇文姓和纳雍新房乡文姓还算勉强传承,但都不见有再传人的传授计划,布所阿铺家族(有龙、张、李、陈、王、安等数十姓)的情况与麻博阿维家族相同,目前仅有威宁新法乡和板底乡的陈林、龙顺峰等为数不多的青年传承人。阿都乃素家族曾在威宁观风、哈喇、牛棚、迤那、黑土河等乡镇形成布摩的“八大先生”,在威宁金钟一带,5~6代人之前,传授了龙场、二塘等乡镇的阿底、迪那、侯大、惹菲等七、八姓弟子,传承人却微乎其微。支纪、阿俄、阿启、法戈、罗卧等数十家族,只留下部分彝文古籍和曾经为布摩的传说。在赫章的财神镇一带,在王子国、王秀平等布摩的鼓励和推动下,布摩的传承尚有一定的基础和希望。情况较为良好的是毕节市大屯乡的三官寨及其周边,布摩的传承有着较为有利的环境,形成了老、中、青的结构,传承人保持在十余人左右。
历史上的毕节地区是彝族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布摩文化发展发育最完善的一块宝地,但到了21世纪,在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与强烈冲击下,布摩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及其严峻的挑战,表现在其传承人青黄不接,断代断层的危险日渐凸显出来,文献、碑刻、口碑等古籍的抢救、保护、利用、传承等都越发显得迫在眉睫,一大批彝家的有识之士更是忧心忡忡。强化培养布摩文化传承人的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2005年8月10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起草了题为《彝文古籍强化速成培训班——布摩再生计划设想》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与相关人士参考,企望能被接受与采纳。在此基础上,2008年,毕节地区彝学会领导专题研究了这件事,对相关方案作了3次以上的可行性论证与修改,到2008年12月20日,产生了《毕节地区彝学会布摩(强化速成)培训班办班方案》。2009年初,旨在抢救、保护和传承彝族布摩文化的首期布摩培训班被地区彝学会列为2009年的七件实事之一,并紧锣密鼓地对方案进行了按部就班的具体实施,在各县彝学会、民宗局的协助下,对学员人选进行了挑选、考核与审察录取。毕节地区彝学会调动与集中利用了大量的社会、师资等资源,2009年3月4日布摩培训班如期开班教学。地区人大工委、地区彝学会的领导对来自威宁、赫章、纳雍、毕节、金沙等县市的22名布摩学员作了动员和鼓劲。到2009年11月15日,毕节地区彝学会首届彝族布摩培训班如期结束培训,学员完成《献酒经》(红事之大类形)、《献茶经》、《早祭与早祭献酒》(宣威与威宁两个版本)、《晚祭与晚祭献酒》(宣威与威宁两个版本)、《迎布摩经》(两个版本)、《解冤经》、《指路经》、《细沓把》、《清理归宿经》、《丧祭大经》(两个版本)、《祭祖经》(两个版本)、《解冤经》(丧祭仪式毕大式)、《清理归宿经》、《丧祭经》(二)、《细札与诺札苏》、《局卓布》、《叟卡陡》、《解灾经》(两部)、《放魂经》、《叟卡占算书》、《献祭土地神》等30部经籍的必修课程。选修《载苏》(三部)、《彝族指路丛书》(七部)、《色特阿育》、《献酒经选》、《献茶经选》、《哭祭》等十四部。通过仪式与布摩基本常识、布神座、各种测算与布摩职能教学;《丧祭经》类与布摩职能教学;小型《祭祖经》类仪式教学;并通过授职,取得布摩资格。这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延缓彝族布摩文化的消亡速度,培养相关传承人,保护濒危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 《迎请布摩书》、《借布摩神力》通常是《彝族丧祭大经》、《消灾祈福大经》内必备的篇章,《彝族丧祭大经》、《消灾祈福大经》是凡做布摩世家都是人手一部的。
[2] 王继超、王子国译《彝族源流》卷十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3] 参见贵州省威宁自治县龙场镇龙丰村李荣林布摩家彝文抄本《策尼勾则》一书。
[4] 根据贵州省威宁龙场刘松林布摩家原书、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第717号藏书翻译。
[5] 根据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拖沟已故布摩禄小玉家所藏的《迎布摩献酒经》一书翻译。
[6]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点校《大定府志·旧事志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
[7] 参见光绪《黔西州续志·土目姓氏仪理论》等
[8] 见马学良《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
[9] 王继超主编《布默战史·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
[10] 王继超主编《布默战史·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
[11] 王继超主编《布默战史·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
